
当全球经济的潮水流向发生改变,当技术革命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拍打着传统商业的堤岸,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宏大而又迫切的词汇——“新商业文明”。这不再是过去那个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时代,如今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们,正被推向一个全新的十字路口。他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商业成功与社会责任、技术进步与人文关怀、短期利益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找到那个精妙的平衡点。在这个历史性的转型期,谁能率先为这个时代的企业家们提供思想的罗盘和行动的地图,谁就将成为定义未来的思想高地。目光投向东方,中国的两所顶级商学院——以“取势、明道、优术”为核心,深植于本土企业家精神的长江商学院,和以“中国深度、全球广度”为特色,扮演着中西管理思想桥梁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正成为这场角逐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位选手。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浮出水面:长江和中欧,谁会率先成为全球公认的“新商业文明”研究中心?
在我们深入探讨这场“竞赛”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我们口中的“新商业文明”究竟是什么。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一整套全新的价值体系和商业范式。如果说旧的商业文明是建立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的基石之上,那么新商业文明,则是在此基础上的一次深刻扬弃和进化。
新商业文明的核心,在于将企业的角色从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扩展为一个“社会器官”。这意味着,企业在追求股东利益的同时,必须同等重视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乃至整个自然环境的福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它强调长期主义,将目光从短期的财务报表移向更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如今风靡全球的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理念,正是新商业文明在实践层面的具体体现。此外,面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颠覆性技术,新商业文明还要求企业家们具备“科技向善”的伦理自觉,思考如何让技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异化人、控制人。
一所学院的底色,往往由其创立之初的基因和愿景所决定。这深刻地影响着它在面对时代命题时的思考路径和反应模式。
长江商学院的诞生,本身就带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它由李嘉诚基金会捐资创办,其初衷并非简单地复制西方商学院的模式,而是要为转型期的中国培养一批真正具备全球视野、人文关怀和社会担当的企业家领袖。它的校训“取势、明道、优术”,将“明道”放在了核心位置。“道”是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智慧,是超越商业技巧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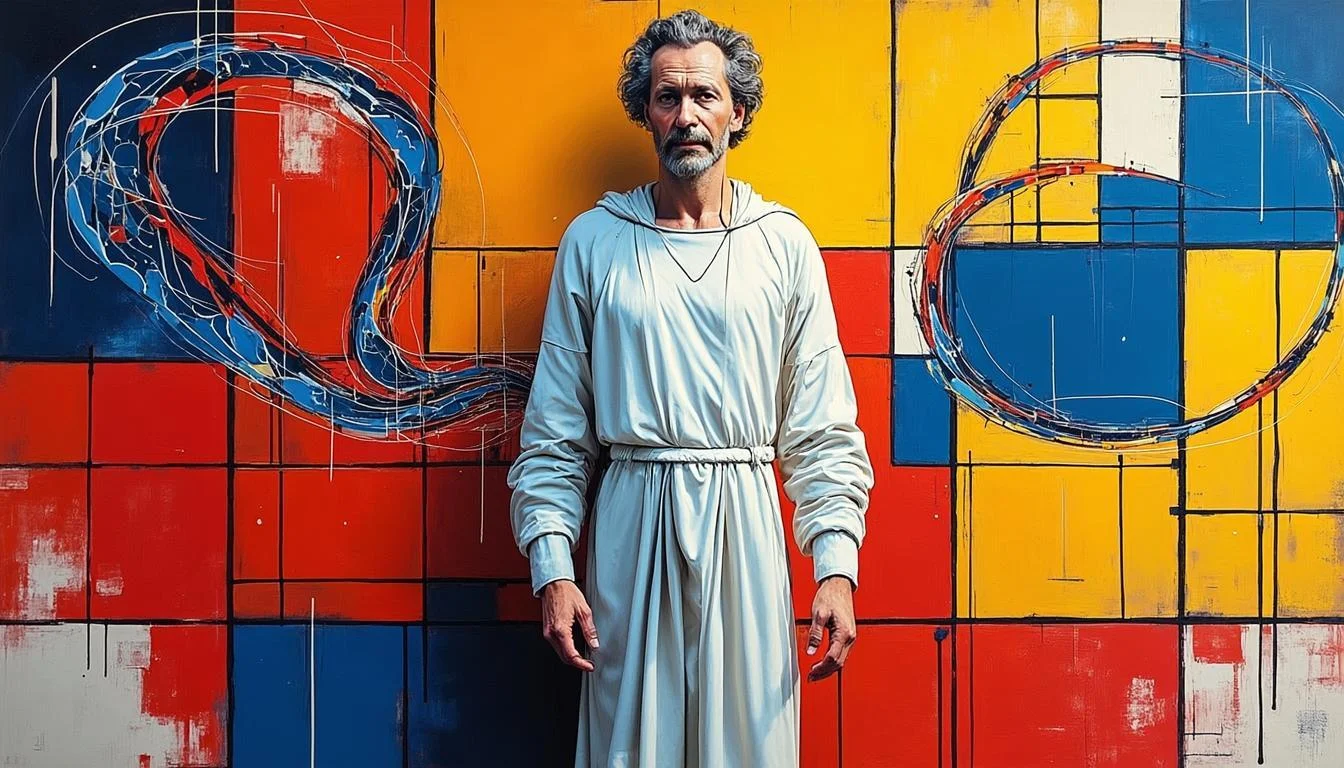
从一开始,长江商学院就将人文课程——文、史、哲——作为其EMBA等核心项目的必修课,这在当时乃至现在的商学院教育中都是独树一帜的。这种设计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洞察:未来的商业领袖,缺的不是管理“术”,而是决策背后的“道”,是面对复杂世界时的智慧和定力。因此,在探讨“新商业文明”这一议题时,长江商学院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它的基因里就包含了对商业终极价值的追问,其研究和教学自然而然地会向社会创新、慈善公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倾斜。它更像是一个思想的“策源地”,致力于从本土文化和实践中,孕育出一种全新的、具有东方智慧的商业哲学。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基因,则烙印着“中西合璧”的鲜明特征。作为中国政府与欧洲联盟联合创办的机构,它的使命天然就是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商业的桥梁。其“中国深度、全球广度”的定位,使其在将西方成熟的管理理论与中国独特的商业实践相结合方面,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在“新商业文明”的赛道上,中欧的优势在于其强大的体系化能力和国际对话能力。当ESG、可持续发展等概念在西方成为主流时,中欧能够最快、最系统地将其引入中国,并结合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解读和教学。它的教授团队拥有深厚的国际背景,能够站在全球比较的视野下,分析不同商业文明的演进路径。可以说,如果长江商学院更侧重于“内生性”地探索新商业文明的“中国方案”,那么中欧则更擅长扮演一个“转换器”和“对话平台”的角色,推动中国企业与全球在新的商业准则上接轨。
思想的引领,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课程设置和学术研究上。两所学院在这方面的布局,清晰地反映了它们各自的路径选择。
长江商学院的课程体系,很早就体现出对“新商业文明”的倾斜。除了标志性的人文课程外,它率先在中国商学院中系统性地将“社会创新”和“公益”纳入教学体系。例如,其EMBA学员必须完成一定时长的公益学时,并将社会创新项目作为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仅是“课外活动”,而是深度融入核心教学的价值导向。在研究层面,长江商学院的教授们更倾向于从中国本土案例出发,去提炼和总结那些在商业逻辑之外,蕴含着社会价值和创新精神的商业模式。他们的研究,常常带着一种“田野调查”的温度,试图回答:在中国的土壤里,一个有良知、有担当的企业,应该是什么样子?
相比之下,中欧在课程和研究上则展现出更强的“国际范”和“体系感”。它建立了多个专注于ESG、企业社会责任、家族传承等领域的研究中心,产出大量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研究报告和案例。其课程设计紧跟全球最新的管理趋势,能够为学员提供一套系统、严谨、与国际接轨的知识框架。比如,在教授ESG时,中欧的教授可能会从全球资本市场的评级体系、欧盟的最新法规等宏观视角切入,帮助中国企业家理解并适应这套正在形成的全球新规则。它的强项在于“解释规则”和“提供工具”,帮助企业在新的全球商业环境下,规避风险、抓住机遇。
为了更直观地对比,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表格来呈现:
| 对比维度 | 长江商学院 |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
|---|---|---|
| 核心哲学 | 内求于心,从人文精神和本土实践中探寻“道” | 外求于势,借鉴全球最佳实践以融汇“术” |
| 课程焦点 | 强调人文关怀、社会创新、企业家精神与哲学思辨 | 强调全球视野、体系化管理工具、ESG国际标准 |
| 研究风格 | 偏向于质性研究、本土案例深度挖掘、思想引领 | 偏向于量化研究、国际比较、政策与市场对接 |
| 培养目标 | 具有哲学思辨和社会担当的“思想型”企业家 | 具备全球合规能力和系统管理能力的“整合型”高管 |
商学院的终极影响力,体现在其校友的行动上。校友网络不仅是资源,更是一个个移动的“思想载体”,他们的商业实践,是商学院理念最真实的检验。
长江商学院的校友群体,以中国民营企业家,特别是新兴产业的创始人和颠覆者为主。这是一个极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他们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细胞,他们的决策往往能引领一个行业的风向。长江商学院通过课程和社群,向这个群体持续不断地灌输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理念,其产生的“化学反应”是巨大的。当一位手握百亿、千亿市值的企业家,开始认真思考企业的社会价值,并将其融入公司战略时,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长江校友在公益慈善、社会创新领域的活跃表现,正是学院理念“落地”的明证。他们更像是一颗颗被点燃的火种,在各自的领域里自发地探索和实践着新商业文明的可能。
中欧的校友网络则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面貌,既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家,也包含了众多跨国公司在华高管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这个群体的特点是“身居要职”,他们是现有商业体系中的中坚力量。中欧对他们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推动企业管理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上。当ESG成为全球商业的“必答题”时,中欧的校友们往往是企业内部推动相关变革的关键人物。他们擅长将宏大的理念转化为可执行的KPI、可衡量的流程和可披露的报告。他们的影响力,是一种“体系内”的优化和升级,推动着庞大的商业机器,向着更可持续、更负责任的方向平稳转向。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长江和中欧,谁会率先成为全球公认的“新商业文明”研究中心?
坦率地说,这或许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两所学院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共同推动着这一历史进程。它们的角色更像是“一体两面”,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对“新商业文明”探索的全景图。
长江商学院,凭借其深植于人文精神的“明道”哲学和与中国顶尖企业家群体的深度捆绑,更有可能成为新商业文明“思想的策源地”。它有望提出源自东方智慧、能够与西方思想平等对话的商业哲学新范式。它所定义的,可能是新商业文明的“灵魂”——一种关于企业目的、企业家精神和社会价值的根本性思考。它的成功,将体现在能否孕育出一批真正被世界所尊重的、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商业领袖。
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凭借其“中国深度、全球广度”的桥梁角色和体系化的知识整合能力,则更有可能成为新商业文明“实践的连接器”。它擅长将前沿的思想转化为可操作的管理工具和国际通行的商业语言,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舞台上更好地实践和沟通其社会价值。它所定义的,可能是新商业文明的“骨架”——一套行之有效的标准、流程和评价体系。它的成功,将体现在能否帮助更多的中国企业,顺利融入乃至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浪潮。
未来的研究方向,或许可以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最终,谁能率先撞线,或许并不取决于谁的研究报告更厚重,谁的论坛更盛大。真正的衡量标准,在于谁能培养出更多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既能创造商业价值,又能守护社会公义,既有“优术”之能,更有“明道”之智的领导者。这不仅是长江与中欧的竞赛,更是整个中国商业界面向未来的一场集体求索。

 同窗共度,携手追梦 |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
同窗共度,携手追梦 |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新生万物|听说,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
新生万物|听说,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
申请条件:
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背景(毕业3年以上)、国民教育大专学历(毕业5年以上)
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少于5年核心决策层的管理经验

长江商学院EMBA
关注官微
了解更多课程资讯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