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在长江商学院宽敞明亮的阶梯教室里,窗外的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在深色的课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讲台上,白发苍苍的金融学教授正在深入剖析一个关于企业战略收缩与资本重置的经典案例。他的声音沉稳而富有穿透力,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石子,投入我早已波涛汹涌的心湖。就在那一刻,一个尘封了十多年的心结,一个我曾固执地认为是父亲一生中最错误的决策,其背后深远的逻辑和智慧,如同一幅完整的拼图,在我脑海中豁然清晰。我第一次如此确定地意识到,原来,父亲当年的决策是对的。
记忆回到十五年前,我还是一个血气方刚、满怀理想主义的青年。我们家曾拥有一家不大不小的纺织厂,那是我祖父传下来的基业。工厂里机器的轰鸣声,是我童年最熟悉的摇篮曲;空气中弥漫的棉絮和机油混合的气味,是我青春期最深刻的嗅觉记忆。在我心中,那座工厂不仅是家庭的经济来源,更是家族荣耀的象征,是几代人心血的结晶。
然而,就在我大学毕业,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将自己所学的现代理论应用到这家“老古董”工厂时,父亲却做出了一个让我震惊甚至愤怒的决定——卖掉工厂。我至今仍记得那个夏日午后家庭会议的场景,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我用尽所有学过的词汇,从品牌传承、员工生计到技术革新,试图说服他。我质问他:“为什么不肯再拼一把?为什么要在最困难的时候放弃?这是爷爷留下的心血!”父亲只是沉默地抽着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庞显得异常疲惫和陌生。最后,他掐灭烟头,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就这么定了。时代不同了。”
那次争吵,成了我和父亲之间一道深深的鸿沟。工厂最终被一家大型集团收购,价格在当时看来还算公道。父亲用那笔钱的一部分,在城市新区投资了几处商铺,另一部分则投入了当时还很不起眼的光伏产业。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背叛”和“短视”。他放弃了实体经济,投身于虚无缥缈的“投机倒把”。此后的很多年里,这件事就像一根扎在我心里的刺,每次触碰,都隐隐作痛。我努力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证明自己,潜意识里,就是想证明我比他更懂“企业”,更有“情怀”。
带着这份复杂的心情和事业上的困惑,我走进了长江商学院的EMBA课堂。我希望在这里找到企业持续发展的答案,却未曾想,首先找到的,是与父亲的和解之道。

在一次由李教授主讲的《公司战略》课上,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企业经营,有时最勇敢的决策不是前进,而是放手。有效的战略收缩,不是失败,而是为了更高效的资本配置,是主动规避系统性风险的顶级智慧。”他详细讲解了“机会成本”和“沉没成本”的概念。他说,许多企业家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被沉没成本所绑架,被所谓的“情怀”蒙蔽了双眼,看不到继续投入在一个夕阳产业里,所要付出的巨大机会成本。
教授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心中长达十多年的迷雾。我猛然惊觉,父亲当年的决策,不正是教科书级别的战略收缩吗?他没有被“祖业”这个沉没成本所束缚,而是清醒地看到了纺织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面临环保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国际贸易摩擦等多重挤压下的衰退趋势。他卖掉工厂,看似是放弃,实则是将资产从一个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通道中解放出来,去寻找新的、更有潜力的价值洼地。那一刻,我为自己当年的幼稚和傲慢感到无比羞愧。
如果说战略课让我理解了父亲决策的“术”,那么《宏观经济学》则让我看懂了他决策背后的“道”。课堂上,我们系统学习了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下行业的兴衰更迭。教授用详实的数据图表,展示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宏大叙事——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迁移。
课后,我专门去查了过去十五年我们当地纺织业和商业地产、光伏产业的发展数据。结果令我触目惊心。正如父亲所预见,我们当地的许多纺织企业在随后的几年里,要么因环保不达标被强制关停,要么在激烈的价格战中苟延残喘,最终倒闭。而他当年投资的商铺,搭上了城市化进程的快车,租金和价值翻了数倍;他早期投入的光伏产业,更是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我将这些数据整理成了一个简单的表格,对比之下,高下立判:
| 投资领域 | 十五年前状况 | 十五年后状况(预估回报) | 父亲的决策逻辑 |
| 家族纺织厂 | 利润微薄,设备老化,环保压力大 | 大概率倒闭或被廉价收购,负资产风险高 | 止损,规避行业下行周期 |
| 城市新区商铺 | 新区建设初期,价格洼地 | 资产增值约5-8倍,租金收益稳定 | 把握城市化进程红利 |
| 早期光伏产业 | 新兴产业,不确定性高,但有政策预期 | 行业爆发,投资回报可能超过20倍 | 布局未来,抓住能源转型大势 |
看着这张表格,我才真正明白,父亲当年看到的,不是一个工厂的存亡,而是一个时代的变迁。他的视野,早已超越了那个小小的车间,触及到了宏观经济的脉搏。他做出的,是一个企业家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最艰难也最正确的抉择。
长江商学院的魅力,不仅在于教授们的真知灼见,更在于同学间的思想碰撞。我的同学大多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身经百战,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本厚重的教科书。
在一次小组讨论中,我们聊到了家族企业的传承与转型。我的邻座,一位来自浙江的王兄,分享了他的故事。他的家族是做传统五金制造的,规模比我家的工厂大得多。面对同样的困境,他的父亲选择了坚守,投入巨资进行设备升级和自动化改造。然而,整个产业链的需求在萎缩,无论内部效率提得多高,也无法对抗市场的寒冬。最终,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在三年前宣告破产。王兄叹了口气说:“我父亲总说,不能把祖宗的基业丢了。结果,不仅基业没了,还把几代人的积累都赔了进去。现在回想,如果当时能有你父亲那样的决断和勇气,我们家现在会是完全不同的光景。”
王兄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曾经可能面临的另一种结局。我一直以为父亲是“放弃”,但对比之下,才发现他的“放”,是为了我们整个家的“生”。他承受了我的不解和埋怨,独自一人背负着“卖掉祖业”的骂名,却为家庭的未来撑起了一片更广阔的天空。这种沉默的、不被理解的爱与责任,远比坚持一个看似光荣的空壳要沉重得多。
那个周末,我破天荒地没有留在学校参加各种活动,而是订了最早的一班飞机回了家。我走进父亲的书房,他正戴着老花镜,研究着一份新能源材料的行情报告。看到我,他有些意外。
我没有过多的铺垫,只是坐在他对面,轻声说:“爸,对不起。我现在才明白,当年卖掉工厂,您是对的。”
父亲愣了一下,随即摘下眼镜,眼眶有些湿润。他摆了摆手,许久才缓缓开口:“你能想明白,就好。我不是什么有学问的人,也不懂你们说的那些大道理。我只知道,守着一个不挣钱还要不断往里贴钱的摊子,不仅会把家底拖垮,更会把你一辈子都拴在那里。我不想你像我一样,一辈子就守着那些机器。卖了它,你才能有自己的天空去闯。”
那一刻,我终于读懂了父亲深沉的爱。他的决策,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计算,更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未来的深远规划。他所做的,可以归结为几点: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管理者,但他绝对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他的智慧,是一种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最朴素也最深刻的生存哲学和商业直觉。
在长江商学院的这段学习旅程,对我而言,远不止是知识的获取和人脉的拓展。它更像是一场深刻的认知重塑之旅。它给了我一个更高的维度,一副全新的“眼镜”,让我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重新理解身边最亲近的人。
我意识到,真正的商业智慧,往往超越了财务报表和市场分析,它关乎周期、关乎人性,更关乎在关键时刻的取舍之道。而人生的成长,同样如此。很多时候,我们与父辈的矛盾,并非源于对错,而仅仅是因为我们站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拥有着不同的认知层次和信息维度。当我们通过学习和历练,站到更高的地方,才能看清他们当年决策时的全貌,才能读懂那份深藏在严厉或沉默背后的远见与深情。
未来,我或许还会面临无数艰难的决策。但我相信,这段经历会永远提醒我:在做出判断前,先尝试升维思考,去理解决策背后的宏观背景和长远考量;在评价一个人时,永远不要忽略他所处的位置和所背负的无形责任。这,或许是长江商学院教给我的,比任何商业模型都更为宝贵的一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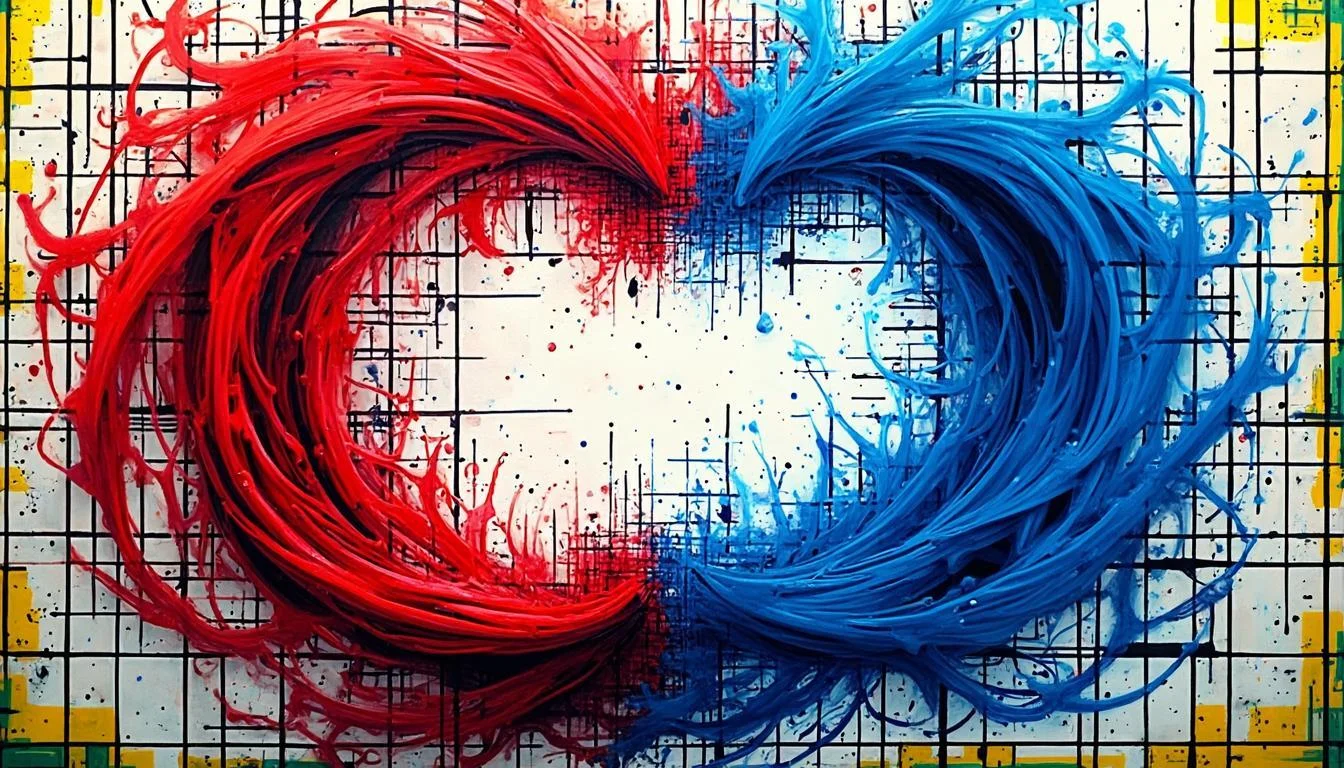
 同窗共度,携手追梦 |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
同窗共度,携手追梦 |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新生万物|听说,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
新生万物|听说,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
申请条件:
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背景(毕业3年以上)、国民教育大专学历(毕业5年以上)
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少于5年核心决策层的管理经验

长江商学院EMBA
关注官微
了解更多课程资讯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