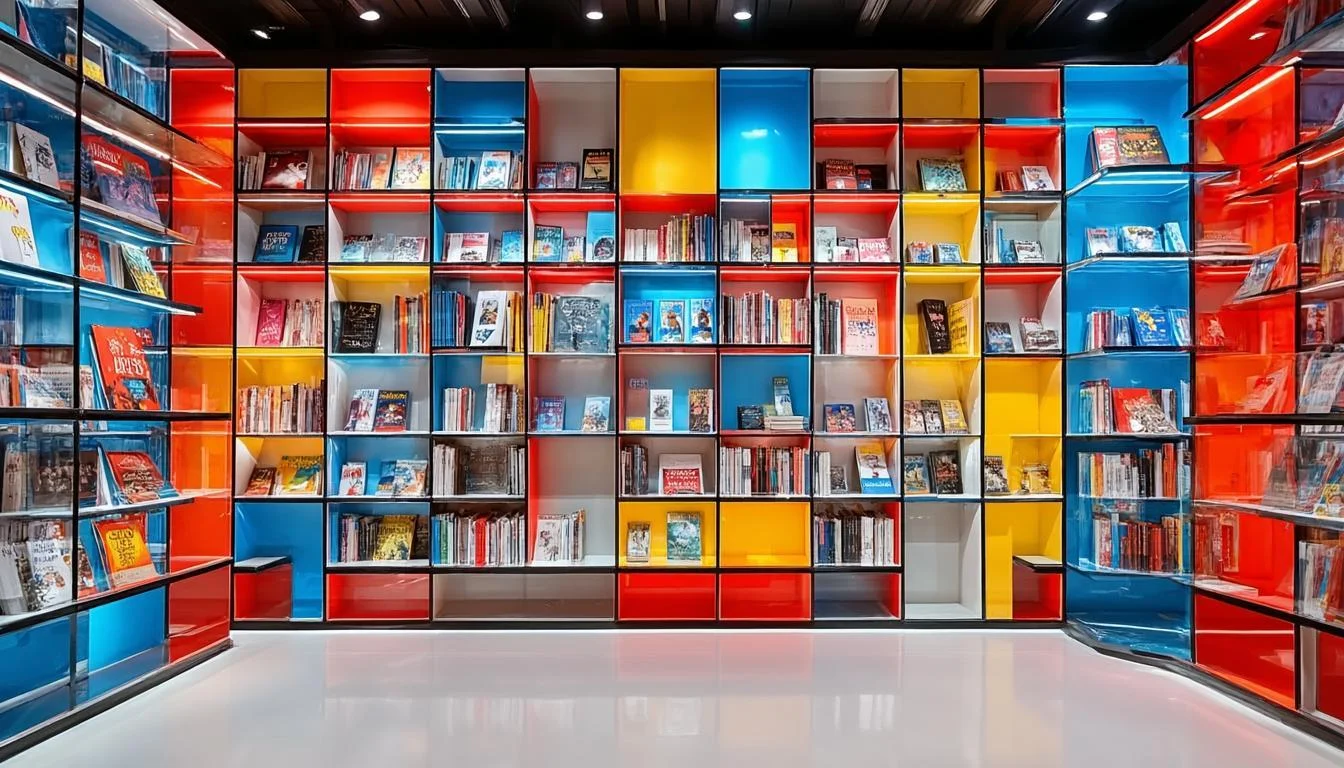
我曾一度为自己的管理风格感到自豪——高效、精准、结果导向。作为一家快速发展公司的部门负责人,我信奉数字和KPI,认为管理就是将复杂的任务拆解成清晰的指令,然后像精准的钟表匠一样,确保每一个齿轮(我的员工)都能在预设的轨道上分毫不差地运转。直到在一次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后的同学小聚上,一句不经意的闲聊,像一颗小石子投进我自以为平静无波的心湖,激起的涟漪却最终汇成了足以颠覆我认知体系的巨浪。
那是一个轻松的周五晚上,几位同学在讨论各自企业遇到的挑战。我照例分享了我们团队如何通过优化流程,提前完成了季度目标。在一片赞许声中,邻座的老李,一位性格爽朗、做传统制造业的同学,拍了拍我的肩膀,半开玩笑地问了一句:“老王,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把任务和KPI说清楚,团队就能自己跑起来了?”我下意识地点点头:“当然,清晰的目标和严格的执行是效率的保障。”他笑了笑,没有再多说,但就是这句看似平淡无奇的话,却在我脑海里反复回响,让我开始了一场深刻的自我审视。
在被点醒之前,我的管理世界是二维的,由“任务”和“时间”这两个坐标轴构成。每个项目都被我视作一个待攻克的堡垒,而团队成员则是执行战术的士兵。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发布指令、设定DDL(截止日期)、检查进度、复盘结果。我很少,或者说几乎从不与团队成员谈论工作以外的事情。我认为,工作场所就应该纯粹,聊家常、谈理想,那是浪费时间,会稀释专注度,甚至带来不必要的情感纠葛,影响专业判断。
我坚信,对员工最大的负责,就是为他们提供清晰的成长路径(体现在晋升和薪酬上)和强大的平台资源。只要我能带领他们打胜仗,分到足够多的战利品,他们的满意度和忠诚度自然会高。因此,我的会议总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我的邮件总是言简意赅,只列要点。团队的氛围也因此变得非常“职业”——安静、有序,每个人都像一台精密的仪器,默默地完成自己的部分。我曾将这种“零噪音”的环境,视为我管理能力的最佳证明。
老李那句“团队就能自己跑起来了”,其潜台词我后知后觉才品味出来:一个只会“自己跑”的团队,是没有灵魂的,它只是在惯性下运动,而非主动地、创造性地奔跑。我猛然意识到,我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仅仅是“管理”(Management),而完全忽略了“领导”(Leadership)。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言:“管理是正确地做事,而领导是做正确的事。” 我痴迷于前者,确保每一件事都按照最高效的方式被完成,却从未真正思考过,如何激励一群人,让他们发自内心地想去做“正确的事”。

我的团队,表面上看起来高效运转,实际上却可能是一盘散沙。员工们执行命令,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职责,是为了KPI和奖金,而不是因为他们认同这项事业的价值,不是因为他们对团队有归属感。我构建了一个完美的任务执行系统,却亲手关闭了与团队成员之间的人性化连接。这个盲区如此巨大,以至于我身处其中多年,却从未察觉,直到被一个局外人的无心之言轻轻戳破。
从财务报表和项目进度表上看,我的部门无可挑剔。我们总能按时甚至提前交付成果,数据表现亮眼,是公司里的明星团队。这也是我过去自信的根源。我用结果证明了我的方法的有效性,任何对我的管理方式提出的潜在质疑,似乎都会在这些漂亮的业绩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我把这种模式总结为“职业化驱动”,并一度想在公司内部推广。
然而,这种纯粹以效率为导向的管理模式,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其成本却是隐藏在水面之下的。就像一座冰山,人们只看到了那浮在水面上的十分之一的辉煌,却忽略了水下那支撑着一切、也潜藏着巨大风险的十分之九。
回到公司后,我开始带着新的视角观察我的团队。我发现,那种过分的安静,其实是一种沉默的警报。在我的“高压”和“高效”氛围下,隐藏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平时被光鲜的业绩所掩盖,但却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引爆。
我试着将这些隐形成本具象化,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表格:
| 表面优势(冰山之上) | 隐形成本(冰山之下) |
| 任务完成速度快:指令清晰,执行力强。 | 缺乏心理安全感:员工害怕犯错,不敢提问和挑战,担心暴露自己的“无能”。 |
| 团队沟通成本低:没有闲聊,直奔主题。 | 创新能力被扼杀:没有人愿意提出“不成熟”的想法,因为那看起来“不高效”,甚至“愚蠢”。 |
| 个人责任明确:KPI清晰,奖惩分明。 | 协作精神薄弱:“自扫门前雪”文化盛行,跨岗位的协作仅限于流程要求,缺乏主动支持。 |
| 产出稳定可预测:一切都在计划内。 | 员工敬业度低,离职风险高:员工只是在“出卖”时间换取薪水,缺乏情感连接,一旦有更好的机会便会毫不犹豫地离开。 |
哈佛商学院教授艾米·埃德蒙森(Amy Edmondson)提出的“心理安全感”(Psychological Safety)概念,完美地解释了我团队的困境。她认为,心理安全感是团队成员相信他们可以承担人际风险的共同信念。在一个缺乏心理安全感的环境中,即使是最有才华的员工,也会选择明哲保身,而不是冒险创新。我所营造的“高效”环境,恰恰是心理安全感的最大杀手。员工们戴着专业的面具,内心却充满了不确定和疏离感。
这次点醒,对我而言,不亚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我意识到,我的管理世界观需要从“以事为中心”彻底转变为“以人为中心”。这并非要我放弃对效率和结果的追求,而是在追求的过程中,必须将“人”这个最大的变量,也是最大的能量源,置于核心位置。团队不是机器,而是生态系统。一个健康的生态,需要阳光、空气和水,而不仅仅是化肥和农药。
在长江商学院的课堂上,教授们反复强调“取势、明道、优术”。我过去沉迷于“优术”,即优化管理技巧和工具,却忽略了“明道”,即理解管理的本质和人性。真正的领导力,是激发善意和潜能的艺术。它要求领导者从一个任务的分配者,转变为一个意义的赋予者、团队的服务者和文化的塑造者。
理论的顿悟必须付诸实践。我开始笨拙但真诚地做出改变,这些改变起初甚至让我的团队成员感到不适应,但坚持下来,效果是显著的。
在转变的过程中,我发现所有改变的核心,都指向一种能力——共情力(Empathy)。在过去的我看来,“共情”是一个非常感性甚至有点软弱的词,与商业世界的残酷和理性格格不入。我曾错误地认为,共情就是同情,就是做“老好人”,为了照顾情绪而牺牲原则。
但真正的共情,是一种认知能力,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感受、思维和动机,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有效沟通和决策的能力。它不是放弃标准,而是用更人性化的方式去达成标准。它不是“和稀泥”,而是像一位高明的医生,通过精准地理解病人的感受和陈述,才能做出最准确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在管理中,共情力能帮助我理解员工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处理表面症状。
当我开始运用共情力去领导团队时,奇妙的化学反应发生了。团队的氛围不再是死气沉沉的安静,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建设性的安静与热烈的讨论交织的状态。会议上,大家开始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直接挑战我的想法。私下里,同事间的互助明显增多,大家开始主动分享资源和经验。
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员工眼中久违的光。他们开始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创造力和热情。一位过去只做“分内事”的资深工程师,主动发起了一个技术优化项目,仅仅因为他在与客户的交流中,共情到了对方的一个痛点。这种由内而外的驱动力,是任何KPI都考核不出来的,却是团队能够持续创造卓越价值的根源。这印证了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在《情商》一书中的观点:共情是构成卓越领导力的核心要素之一。
回望过去,从那个只信奉数字和流程的“管理者”,到今天努力成为一个懂得倾听和关怀的“领导者”,这段旅程的起点,仅仅是EMBA同学在一次轻松聚会上的一句无心之言。它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认知中最坚固的一扇门,让我看到了门后那个被我长期忽视的、关于“人”的广阔世界。
这次点醒让我深刻理解到,卓越的管理,从来不是“事”与“人”的二选一,而是两者的完美融合。高效的流程和系统是骨架,而人性的关怀和激励则是血肉。一个只有骨架的组织,僵硬而脆弱;一个只有血肉的组织,松散而无力。唯有骨血相连,才能造就一个健康、强大且富有生命力的有机体。这次经历也让我更加珍视在长江商学院这样的平台上的学习和交流,因为真正的智慧,往往就隐藏在与优秀同行的思想碰撞和不经意的点拨之中。
我的这场管理修行仍在继续。从“管理”到“领导”,是一条永无止境的道路。但至少,我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对于所有行走在管理道路上的同行者,我的建议是:请务必时常停下来,审视一下自己是否存在类似的盲区。有时候,最深刻的变革,或许就源于你最意想不到的一次提醒,源于你愿意真正俯下身,去倾听那些关于“人”的声音。

 同窗共度,携手追梦 |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
同窗共度,携手追梦 |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新生万物|听说,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
新生万物|听说,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
申请条件:
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背景(毕业3年以上)、国民教育大专学历(毕业5年以上)
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少于5年核心决策层的管理经验

长江商学院EMBA
关注官微
了解更多课程资讯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