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一位在传统行业摸爬滚打了半生,凭借着胆识、人脉和对市场敏锐的嗅觉建立起自己商业帝国的企业家,在酒过三巡的饭局上,听到邻座的“小年轻”们热火朝天地讨论着AIGC、私域流量和颠覆式创新时,内心是否会掠过一丝不安?这种不安,源于对未知的恐惧,也源于对自身商业模式可能被时代淘汰的焦虑。于是,将目光投向那些顶尖的商学院,比如声名显赫的长江商学院,期望通过其精心设计的“创新课程”,为自己这艘正在经历风浪的“老船”换上新的引擎。但这艘船,真的能通过几堂课、几次游学,就学会如何在数字化的新航道上乘风破浪吗?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长江商学院这类顶级学府的创新课程,确实能够为传统企业家提供一套系统化、结构化的创新知识体系。这就像是给一个经验丰富但只会“凭感觉开车”的老司机,递上了一本详尽的《车辆工程学》和《高级驾驶技巧手册》。他或许已经能应对路上的大部分情况,但手册能让他明白,为什么在某个特定角度转弯最省力,为什么引擎会在某种状况下发出异响。
在课程中,企业家们会接触到当今全球前沿的创新理论与工具。从“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的用户共情与原型测试,到“精益创业”(Lean Startup)的“构建-衡量-学习”循环,再到“蓝海战略”(Blue Ocean Strategy)的价值创新曲线。这些理论框架,将“创新”这个看似玄妙、依赖灵光一闪的概念,拆解成了一系列可以学习、可以操作的步骤和方法。企业家们会通过大量的商业案例分析,看到特斯拉是如何颠覆百年汽车工业的,Netflix是如何从一家DVD租赁小公司成长为流媒体巨头的。这些案例,尤其是长江商学院深入研究的中国本土案例,为他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板和可以规避的“坑”。
更重要的是,课程帮助企业家们建立了一套共同的“创新语言”。当他们回到自己的企业,想要推动变革时,不再是模糊地喊着“我们要创新!”,而是可以清晰地提出:“我们先用设计思维的方法,深入访谈一下我们的核心用户群体,看看他们真正的痛点是什么。”或者“这个新项目风险太高,我们能不能采用精益创业的模式,先做一个最小可行性产品(MVP)投入市场,快速验证我们的商业假设?”这种语言上的统一,是推动组织内部创新的第一步,它让沟通变得更高效,让目标变得更清晰。
如果说知识体系是创新的“术”,那么思维模式的重塑,则是创新的“道”。这或许是长江商学院的课程能带来的更深层次、也更具挑战性的价值。传统企业家,尤其是制造业、房地产、传统零售等领域的成功者,他们的成功往往建立在对“确定性”的追求和掌控之上:稳定的供应链、可控的成本、可预测的市场回报。他们的思维模式是线性的、严谨的,甚至是有些固化的。
然而,创新的本质,恰恰是拥抱“不确定性”。它要求企业家从一个精于计算的“管理者”,转变为一个乐于探索的“探险家”。长江商学院的课程设计,往往通过高强度的互动、跨界的思想碰撞以及对失败案例的深入剖析,来冲击这种固有的思维定式。当一位做传统机械制造的“老总”,与一位90后AI公司的创始人、一位顶尖的风险投资人坐在一起,为一个虚拟的创业项目争论得面红耳赤时,他所受到的冲击是巨大的。他会发现,原来商业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玩法,原来“失败”可以不被视为耻辱,而是获取认知、快速迭代的宝贵学费。

这种环境的营造,是思维重塑的关键。在由教授、同学、校友组成的强大“场域”中,企业家们会不断被挑战、被启发。他们会听到这样的观点:“真正的护城河不是你的工厂和渠道,而是你持续创新的能力。”他们会参与到这样的讨论中:“如果你的核心业务明天就消失了,你还能靠什么活下去?”这些问题,在日常的经营中很少有人敢于向他们提出。久而久之,一种新的思维习惯开始形成:从“如何把今天的事情做得更好”,转变为“如何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明天”;从规避风险,转变为管理风险下的探索。这是一种从“守业”到“创业”的心态回归。
不可忽视的是,同学圈子带来的影响。在长江商学院,你的同学可能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和你一样的传统行业巨头,也有在新经济领域叱咤风云的后起之秀。这种多元化的构成,本身就是一本活的教科书。看到身边曾经同样传统的同学,在学习后回到企业大刀阔斧地进行数字化转型,并初见成效,这种“同侪压力”比任何教授的敦促都来得有效。而那些新经济领域的同学,他们天然的互联网思维、对用户体验的极致追求、快速迭代的工作方式,都会像一面镜子,照见传统企业在组织架构、企业文化上的滞后之处。
尽管课程提供了先进的工具和颠覆性的思维,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是:从商学院的课堂,到自己企业的会议室,中间隔着一道巨大的实践鸿沟。企业家在课堂上学得热血沸腾,回到公司却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道“次元壁”体现在多个层面。
首先是企业文化的阻力。创新往往意味着对现有利益格局的挑战。一个旨在提升效率的数字化系统,可能会让某些掌握着信息孤岛的老员工感到权力被削弱;一个探索新商业模式的小团队,可能会被看作是“不务正业”,消耗着公司核心业务赚来的宝贵资源。企业内部已经形成的“免疫系统”,会本能地排斥这些“异物”。企业家本人即便想推动变革,但如果中高层管理者思维僵化、基层员工习惯于按部就班,那么再好的蓝图也只是纸上谈兵。
其次是资源配置的困境。创新需要投入,而且往往是短期内看不到明确回报的投入。对于习惯了计算投入产出比(ROI)的传统企业而言,为一项充满不确定性的新业务持续“烧钱”,是一个艰难的决策。企业家在课堂上学到要容忍失败,但回到现实中,面对董事会的质询和财务报表的压力,他还能否坚持为试错项目提供宽松的环境和充足的弹药?这考验的不仅是他的认知,更是他的决心和在组织内部的权威。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种冲突,我们可以看看下面的对比:
| 维度 | 长江商学院课堂所学 | 传统企业现实 |
| 对待失败 | 失败是学习的机会,是创新的“必要成本”。 | 失败是需要问责的事故,影响绩效和奖金。 |
| 决策方式 | 基于用户洞察和快速实验,小步快跑,快速迭代。 | 基于历史数据和领导经验,层层审批,追求万无一失。 |
| 组织结构 | 推崇敏捷、跨职能的小团队,网络化协作。 | 森严的科层制,部门墙高耸,跨部门协作困难。 |
| 人才观 | 鼓励“T型人才”,奖励敢于挑战、提出异见的人。 | 偏爱“螺丝钉”式的执行者,强调忠诚和服从。 |
可见,企业家学到的“屠龙之术”,很可能回到公司后发现,要面对的不是一条“恶龙”,而是一个盘根错节、难以撼动的复杂生态系统。因此,长江商学院的课程能否奏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位企业家是否具备将所学“翻译”并“植入”到自己企业土壤中的能力和魄力。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长江商学院的“创新课程”能让一个传统企业家真正学会创新吗?
答案是复杂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无法直接“教会”创新,但它是一个极其有效的“催化剂”。
长江商学院的课程,就像一个高浓度的营养液。它能为企业家这颗渴望生长的“种子”提供最顶级的养分:
然而,课程本身并不能代替企业家去行动。它不能解决企业内部的政治斗争,不能代替企业家做出艰难的资源取舍,更不能保证每一次创新尝试都能成功。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言:“创新更多的是一项艰苦、专注、有目的的工作,而不是天才的灵光一闪。” 商学院的课程,正是为了让这项“艰苦的工作”变得有章可循。
最终,能否真正学会创新,关键在于企业家本人。他是否愿意在课程结束后,将自己“归零”,以一个创业者的心态重新审视自己的企业?他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将学到的理论与自己企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而不是生搬硬套?他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挑战既得利益者,去推动一场自上而下的文化变革?
因此,长江商学院的创新课程,对于一位有变革决心、有学习能力、有行动魄力的传统企业家来说,无疑是价值连城的。它能极大地缩短其认知迭代的时间,提高其创新决策的成功率。但对于那些仅仅希望通过一张文凭、几句时髦术语来装点门面,而没有勇气直面内部问题的企业家而言,这笔昂贵的学费,最终可能只会换来几本精美的讲义和一张通讯录而已。课程结束的那一天,不是学习的终点,而是真正考验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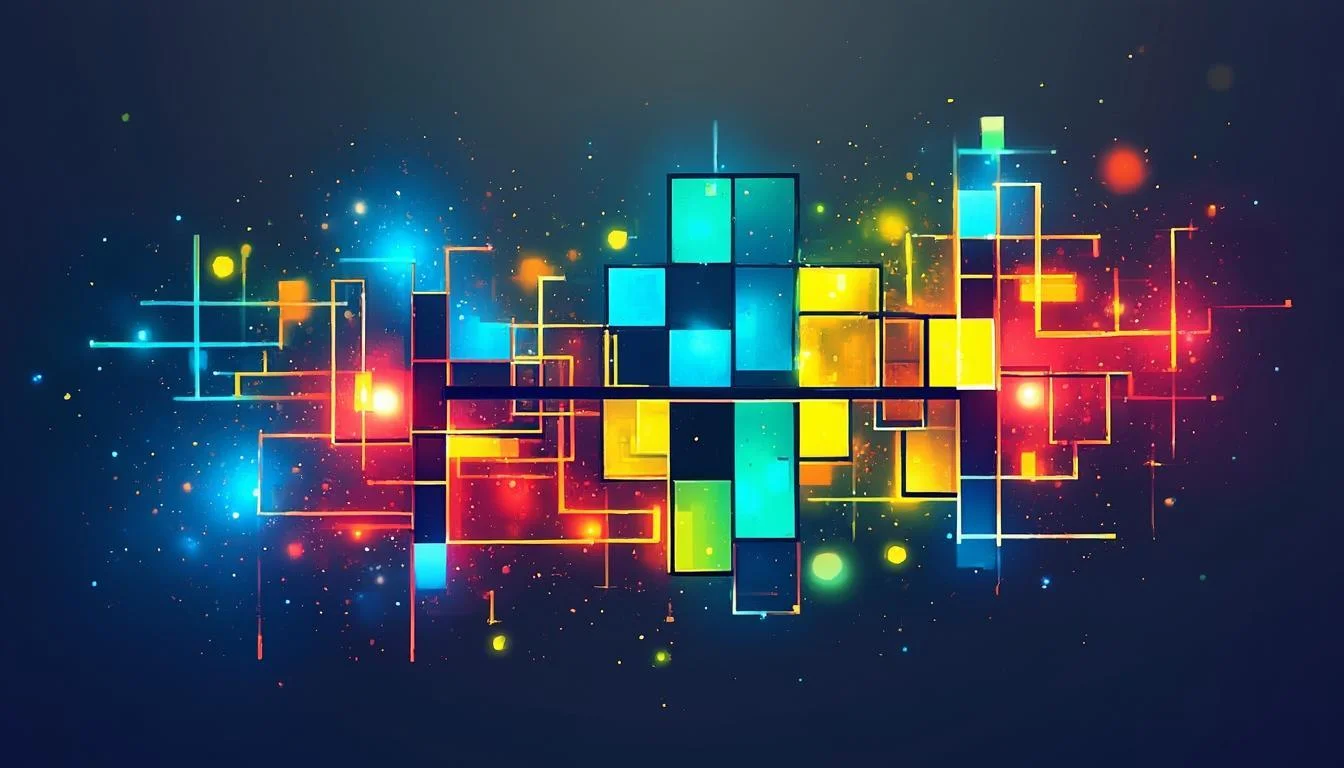
 同窗共度,携手追梦 |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
同窗共度,携手追梦 |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新生万物|听说,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
新生万物|听说,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
申请条件:
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背景(毕业3年以上)、国民教育大专学历(毕业5年以上)
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少于5年核心决策层的管理经验

长江商学院EMBA
关注官微
了解更多课程资讯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