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坦白说,在踏入长江商学院EMBA课堂之前,我对“人文”这两个字的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在我的世界里,商业就是商业,是关于数字、报表、战略和回报率的精确科学。利润、市场份额、用户增长,这些才是衡量成功的标尺。至于哲学、历史、艺术?那似乎是象牙塔里的风花雪月,是与我们这些在商场上摸爬滚滚的人隔着一层厚厚玻璃的遥远风景。我甚至带着一丝理科生特有的偏见,认为那是一种“无用之学”,是成功之后附庸风雅的点缀。然而,我未曾预料到,正是在长江,这些我曾经嗤之以鼻的“无用之学”,最终竟成了我整个EMBA学习旅程中,最深刻、最宝贵,也最让我心动的收获。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拿到课程表时的心情。当“中国哲学与人生”、“艺术史与审美”、“全球史中的领导力”这些课程赫然在列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困惑,甚至夹杂着一丝不解和抗拒。我们是一群身经百战的企业家和高管,我们渴望学习的是如何带领企业穿越经济周期,是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开疆拓土,是如何运用最前沿的金融工具进行资本运作。我们为什么需要在这里坐下来,讨论几千年前的孔子和庄子,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或是回溯某个早已消亡的古老帝国的兴衰?
这种困惑感在最初的几堂课上达到了顶峰。当教授在讲台上引经据典,从《论语》谈到《道德经》,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谈到宋明的理学心学时,我感觉自己像个误入异世界的闯入者。周围的同学们,个个都是在各自领域叱咤风云的人物,此刻却都安静地聆听着这些似乎与“赚钱”毫无关联的智慧。我努力地想把“无为而治”与我的KPI考核联系起来,想把“知行合一”套用在项目管理流程上,却发现如此生搬硬套显得格外滑稽和笨拙。那段时间,我内心充满了挣扎:这真的是我需要的吗?这些知识,到底能为我的企业带来什么实际的价值?
转变,发生在一堂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课上。那堂课的主题是分析罗马帝国的衰亡。教授并没有罗列枯燥的年份和事件,而是将罗马帝国比作一个巨大的、复杂的“公司”。他引导我们从组织架构、官僚体系、财政税收、技术创新、外部环境变化等多个维度,去解构这个庞然大物的崩塌过程。他提问:“当一个组织过于庞大和僵化,失去了对外部变化的敏感性,它的‘柯达时刻’会在何时降临?”“当内部的沟通成本和腐败成本,超过了其扩张带来的收益,‘增长的极限’又在哪里?”
那一刻,我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历史,在我的眼前突然“活”了过来。它不再是尘封的故纸堆,而是一个个无比宏大、时间跨度长达数百上千年的商业案例库。罗马的衰亡,不正是关于企业战略僵化、组织臃肿、创新停滞、无法应对颠覆性挑战的终极警示吗?汉武帝的“盐铁专卖”,与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行业垄断问题,何其相似?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其中包含了多少关于改革阻力、利益集团博弈和人性弱点的深刻教训?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每天在企业管理中遇到的所有难题——增长、创新、危机、文化、传承——其实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都以不同的形式反复上演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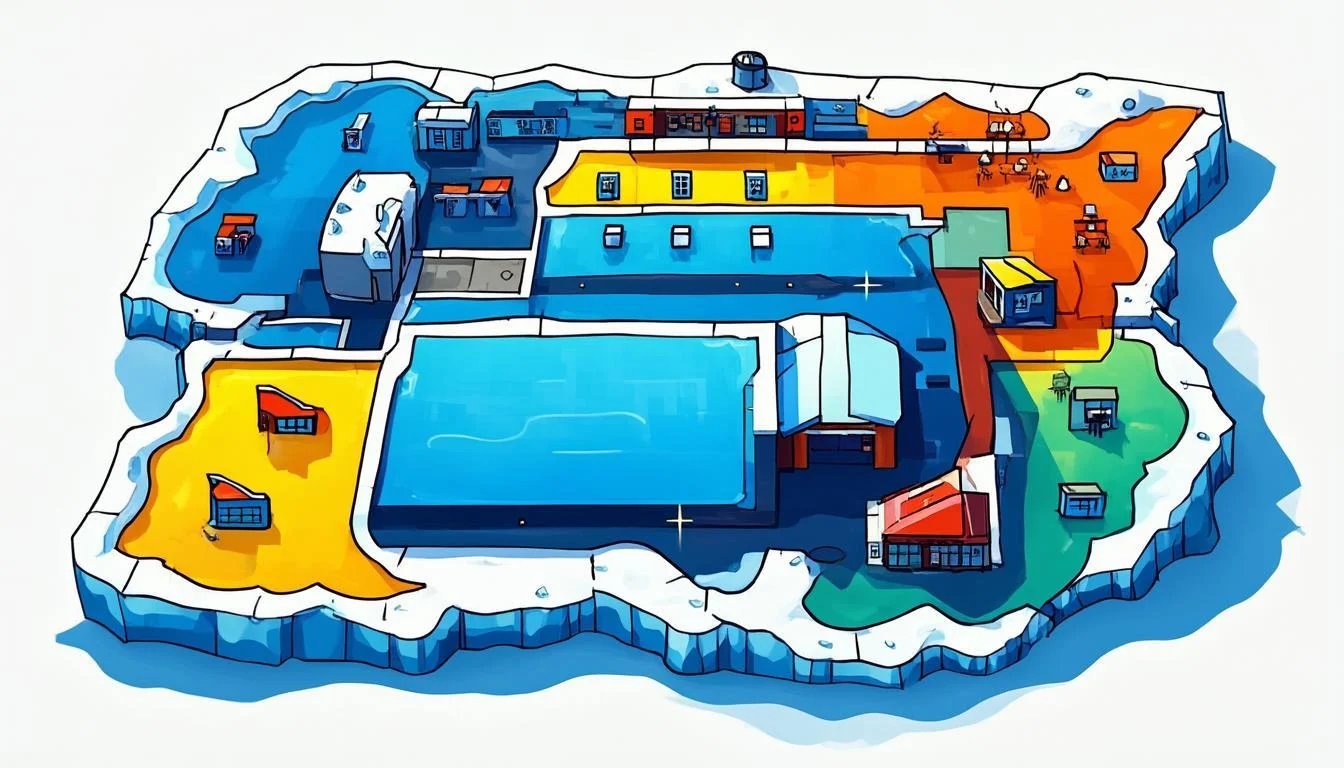
一旦那层认知的壁垒被打破,一个全新的世界便向我敞开了大门。我开始贪婪地吸收着每一堂人文课带来的养分,并惊奇地发现,它们从根本上重塑了我看待商业和管理的思维框架。
过去,我制定公司战略,眼光最多看到未来三到五年,参考的是同行的动态和市场的报告。但学习了全球史之后,我的思考尺度被极大地拉长了。我开始思考“周期”。经济有周期,行业有周期,一个企业的生命也有周期。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帝国,也没有永远领先的企业。这让我对成功保持了极大的警醒和敬畏之心。在公司高歌猛进的时候,我会思考盛唐是如何由盛转衰的,提醒自己警惕“安史之乱”式的内部风险和战略盲点。
长江商学院的教授们非常善于引导我们将历史智慧与当下实践相结合。我们曾在课堂上激烈地讨论,如果用现代企业管理的SWOT分析法去解构清朝的“康乾盛世”,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它的优势(Strengths)是庞大的人口和统一的市场,劣势(Weaknesses)是僵化的制度和科技的落后,机会(Opportunities)是与西方早期全球化的接触,而威胁(Threats)则是内部的人口压力和外部的技术代差。这种跨越时空的“沙盘推演”,远比任何商业案例都来得深刻,它让我们学会了从更宏观、更长远的维度去审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之道。
如果说历史给了我“广度”,那么哲学则给了我“深度”。作为一名CEO,我每天都在做决策。但哲学课让我开始反思:决策的依据是什么?除了商业利益,还有哪些更高的原则?当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发生冲突时,我该如何抉择?这些问题,财务报表给不了答案,市场调研也给不了答案。
学习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我开始重新审视企业文化建设的根基,明白一个组织的凝聚力最终源于共同的价值观。接触道家的“上善若水”,我学会在管理中保持柔韧性,懂得在不确定性中顺势而为,而非一味强求。而西方哲学中对“正义”和“契约精神”的探讨,则让我在处理商业合作和劳资关系时,有了一把更为坚实的伦理标尺。领导力,归根结底是影响人的艺术,而哲学,正是关于“人”的终极学问。它无法直接教你如何提升利润,却能让你成为一个更清醒、更自省、更有定力的领导者,从而在纷繁复杂的商业世界中,行得更稳,走得更远。
艺术课,或许是EMBA课程中最“不食人间烟火”的一门。但它带给我的冲击,却丝毫不亚于其他课程。在一堂关于印象派的课上,教授向我们展示了莫奈的《日出·印象》。他没有过多讲解绘画技巧,而是问我们:“在莫奈之前,所有人都认为水是蓝色的,影子是黑色的。但莫奈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阳光在水面上反射出的万千色彩,看到了物体在不同光线下投射出的紫色和蓝色的阴影。他画出了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这不就是创新的本质吗?创新,就是打破约定俗成的观念,去发现那些被“集体无意识”所忽略的真相和可能性。无论是苹果的乔布斯,还是特斯拉的马斯克,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莫奈”,他们看到了一个被现有范式所遮蔽的、全新的世界。艺术审美训练的,正是一种对细节的敏感、对常规的质疑和对“不同”的欣赏能力。它教会我们跳出固有的思维框架,用一种全新的、充满好奇的眼光去观察用户、审视产品、洞察市场。这种“发现美”的能力,最终会转化为“创造价值”的能力。
回顾这段奇妙的旅程,我深感长江EMBA人文课程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其内容本身,更在于其独特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氛围。
首先是授课的教授们。他们无一不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师。他们不仅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更有一种将阳春白雪化为下里巴人的非凡能力。他们能用最生动的语言,将复杂的哲学概念、晦涩的历史事件、抽象的艺术理论,与我们这些“俗人”的商业实践和人生困惑无缝对接,引发我们强烈的共鸣和深入的思考。他们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智慧的引路人。
其次,是同学间的思想碰撞。在人文课的课堂上,没有标准答案。当一个历史或哲学命题被抛出时,来自不同行业、有着不同背景的同学们会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展开精彩纷呈的讨论。做实业的同学会从制造业的角度解读工业革命,做投资的同学会用资本的眼光分析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做互联网的同学则会从平台的角度探讨罗马的道路系统。这种跨界交流所产生的火花,其价值难以估量。它让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无数种可能性,也让我学会了谦卑地倾听和尊重不同的观点。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这种转变,我整理了如下的对比:
| 思维维度 | 学习人文课之前的我 | 学习人文课之后的我 |
|---|---|---|
| 看待历史 | 一堆与我无关的、枯燥的旧故事。 | 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宏观战略案例库。 |
| 看待哲学 | 空洞的、不切实际的清谈。 | 一把衡量决策、塑造领导力和构建企业文化的伦理标尺。 |
| 看待艺术 | 少数人的高雅爱好,与商业无关。 | 一个训练创新思维、培养非共识能力的重要场域。 |
| 决策模式 | 更依赖数据、模型和短期ROI。 | 在数据和模型之外,会更多地融入历史纵深感、哲学思辨和人性洞察。 |
从最初的全然无知与抗拒,到后来的深深沉醉与热爱,我在长江商学院的人文课堂上,完成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自我蜕变。我曾以为我是来学习“术”的,学习那些能让企业更快、更强的具体方法和工具。但我最终收获的,却是“道”的层面的智慧——一种更宏大的格局、更深刻的洞察和更坚实的内心力量。
正如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言,管理本身就是一门“博雅艺术”(Liberal Art)。一个卓越的领导者,需要的不仅仅是专业技能,更需要广博的知识、独立的人格和深厚的人文素养。在今天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VUCA)的时代,商业竞争早已超越了产品和技术的层面,进入了认知和格局的更高维度竞争。人文知识,恰恰是提升我们认知维度的最佳“武器”。
因此,我由衷地建议所有身处商界的同仁,尤其是那些手握方向盘的企业决策者们,不妨在追逐数字和效率的间隙,为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去亲近人文。它或许无法立刻给你带来一份订单,却能赋予你一种穿越周期的智慧和定力。而对于商学教育而言,我更期待看到像长江商学院这样,将人文教育置于核心地位的模式能够成为一种趋势。因为我们培养的,不应仅仅是精于计算的职业经理人,更应是具有历史感、责任感和创造力的、真正的领导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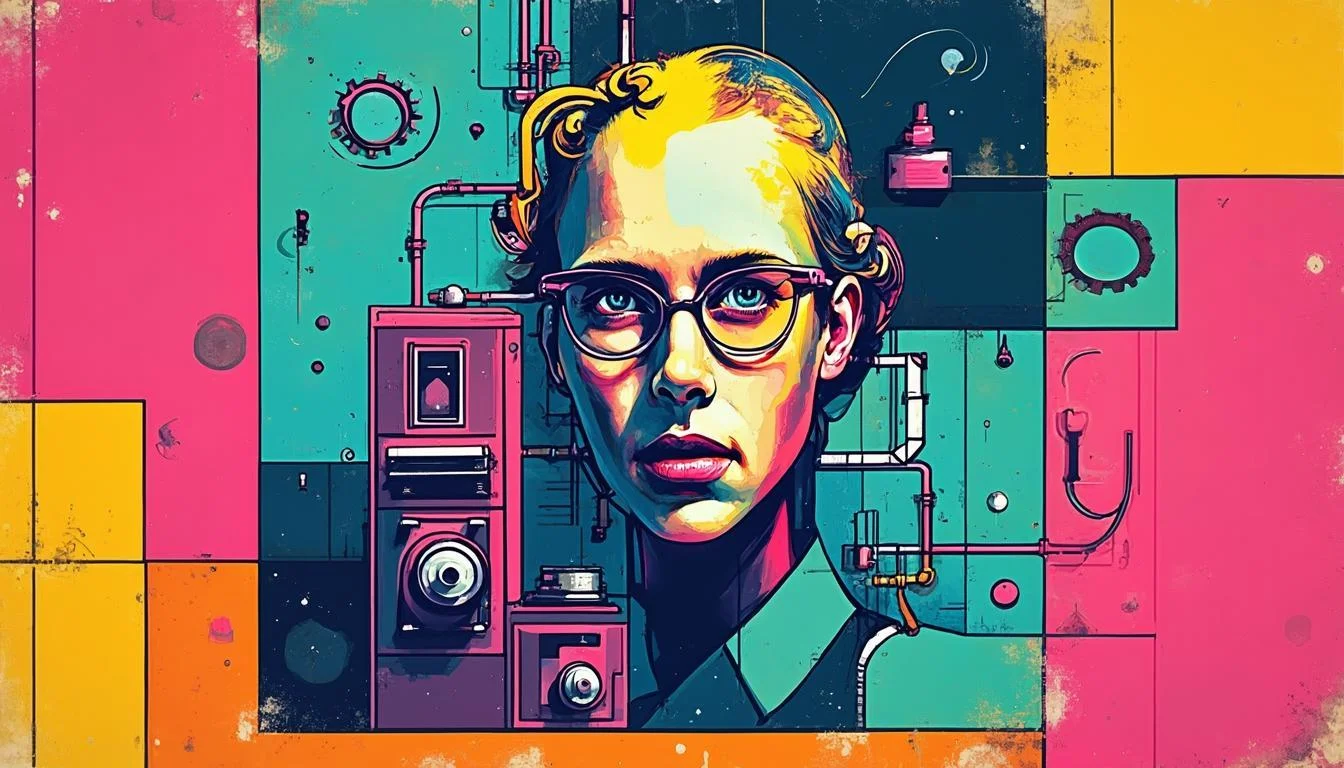
 同窗共度,携手追梦 |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
同窗共度,携手追梦 |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新生万物|听说,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
新生万物|听说,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
申请条件:
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背景(毕业3年以上)、国民教育大专学历(毕业5年以上)
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少于5年核心决策层的管理经验

长江商学院EMBA
关注官微
了解更多课程资讯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