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饭菜香,餐桌上却横亘着一道无形的墙。我和父亲相对而坐,沉默是我们之间唯一的语言。这沉默,像一坛陈了二十年的酒,愈发浓烈,也愈发苦涩。我曾以为,这道墙会永远矗立在我们之间,直到我走进EMBA的课堂。那段学习的时光,像一把意想不到的钥匙,竟打开了我们父子之间尘封二十年的心门。它不仅重塑了我的商业认知,更让我重新认识了我的父亲,最终,我们达成了那场迟到了二十年的和解。
在我的成长记忆里,父亲是权威的化身,也是“固执”的代名词。他白手起家,创立了自己的工厂,一辈子都在和机器、订单、工人打交道。他的管理方式,在我看来,充满了经验主义的武断和不近人情的严苛。我从海外留学归来,满脑子都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新理念,试图在他的工厂里推行绩效考核、流程优化、企业文化建设,但每一次都以激烈的争吵告终。他总是一句话堵回来:“我做了一辈子生意,难道还不比你懂?”
这道鸿沟,看似是新旧观念的冲突,实则是父子之间认知维度的错位。我视他为不懂变通的“老古董”,他视我为夸夸其谈的“赵括”。我们都试图用自己的尺子去丈量对方,结果自然是格格不入。这种挫败感,让我一度选择逃离,与他的事业保持距离,我们之间的交流也因此降至冰点。
然而,在长江商学院的EMBA课堂上,当教授们深入浅出地讲解那些经典的管理理论时,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案例,就是我父亲和他的工厂。在学习“波特五力模型”时,我猛然发现,父亲那些看似“固执”的决定——比如坚持用熟人供应商,拒绝看似更便宜的新渠道——其实是在无形中降低“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并维持稳定的供应链。他强调“现金为王”,对贷款和扩张极为审慎,这不正是“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中,对处于成熟期、面临激烈竞争的企业最稳健的财务策略吗?他对我那些“先进”理念的抗拒,深层原因是对风险的极度敏感,是在用他几十年的血汗经验,为企业的生存保驾护航。
我开始意识到,我曾经引以为傲的理论知识,是悬浮在空中的楼阁;而父亲的“固执”,则是深深扎根于中国这片商业土壤的实践智慧。他没有学过MBA,但他本人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关于中国民营企业从0到1的教科书。那一刻,我对他不再是批判和俯视,而是发自内心的理解与敬佩。我不再纠结于他是否“懂”现代管理,而是开始研究他“为什么”这样做。这种视角的转变,是和解的第一块基石。
过去,我和父亲的沟通模式,可以称之为“冲突型”或“回避型”。我要么是带着改变者、甚至是拯救者的心态,试图说服他、纠正他,结果必然是冲突;要么是心灰意冷,选择沉默,彻底回避与他谈论工作,这又导致了更深的情感隔阂。我们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更缺乏沟通所必需的同理心。

EMBA的学习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大型的“沟通训练营”。我的同学来自各行各业,有成功的创业者,有跨国公司的高管,每个人都有着强大的个人意志和鲜明的观点。在小组案例讨论中,你无法用权威去压制别人,也无法用沉默来解决问题。你必须学会倾听,真正地去理解对方发言背后的逻辑和立场;你必须学会表达,用清晰、有条理的语言,辅以数据和事实,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你更需要学会协作,在不同的意见中寻找共识,最终达成一个最优的团队决策。
一位教组织行为学的教授曾说:“沟通的目的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连接。” 这句话对我触动极大。我反思自己与父亲的交流,我总是想“赢”,想证明我是对的,他是错的。我从未真正尝试去“连接”他,去理解他肩上扛着的几百个家庭生计的重担,去体会他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我只看到了他的“固执”,却没看到他背后的恐惧和责任。
带着这种全新的认知,我开始尝试用新的方式与父亲沟通。我不再一上来就抛出颠覆性的方案,而是从请教开始。我会问他:“爸,最近原材料价格波动很大,我们以前遇到类似情况是怎么应对的?”或者“三车间的李师傅快退休了,您觉得找个什么样的人接替他比较合适?”当我把姿态放低,把他当成一位值得尊敬的“创业导师”时,他那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了。他开始愿意和我分享他当年的创业故事,那些我从未听过的、关于他如何拿到第一笔订单、如何度过资金链断裂危机的细节。我们的谈话,不再是火星撞地球,而变成了温暖的炉边夜话。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我和父亲之间长期的隔阂,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使用着两套完全不同的“商业语言”。他谈论的是“跑业务”、“看行情”、“管工人”,具体而微,充满了市井的烟火气。我谈论的是“赛道”、“壁垒”、“赋能”,抽象而宏大,充满了精英的距离感。我们的话语体系,反映了我们所处时代、所受教育和商业环境的巨大差异。
EMBA的学习,为我提供了一套能够与父亲“同频”的语言系统。这套系统既能容纳宏观的战略框架,也能下沉到具体的运营细节。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套中性的、专业的分析工具,可以超越个人情感和偏见,客观地审视企业的问题。当我能用专业的术语,为他清晰地分析出现金流、库存周转率、客户复购率等核心指标时,他看我的眼神变了。
| 父亲的“土话” | 我的“新词” | EMBA课堂上的“共同语言” |
| “多交朋友,路子才广” | “构建私域流量,提升用户粘性” | “建立和维护利益相关者网络 (Stakeholder Network)” |
| “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 | “精益创业,最小可行性产品 (MVP)” | “成本领先战略与现金流管理 (Cost Leadership & Cash Flow Management)” |
| “做生不如做熟” | “聚焦核心业务,避免盲目多元化” | “企业核心竞争力与业务边界 (Core Competence & Business Scope)” |
这张简单的表格,背后是我和父亲认知世界的巨大变迁。过去,我们鸡同鸭讲;现在,我们可以坐在一起,摊开财务报表,讨论公司的战略转型。我能理解他为何对某些老客户格外宽容(因为他们是公司早期的“天使投资人”),他也能明白我为何坚持要投入资金进行数字化改造(因为这是提升长期“运营效率”的必要投资)。我们不再是观点的对立者,而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们讨论的,是“我们公司”的未来,而不是“你的”或者“我的”主张。
如果说管理理论和沟通技巧是“术”,那么真正让我完成心灵和解的,是EMBA课程中所蕴含的“道”,尤其是长江商学院一直强调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在这里,我遇到的不仅仅是商业奇才,更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一次关于家族企业传承的讨论课上,一位比我年长的同学,一位已经成功接班的“创二代”,分享了他与父亲长达十年的磨合与冲突。他的故事,几乎就是我经历的翻版。他最后说:“我花了十年才明白,父亲想传给我的,不只是一个企业,更是他的生命和尊严。当我开始尝试去守护他的尊严时,企业传承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番话,如同一道光,照进了我内心最幽暗的角落。
我开始反思,我与父亲的争执,真的是为了企业好吗?还是为了证明“我比你强”,为了满足自己年轻气盛的虚荣心?我急于用我的“新”去覆盖他的“旧”,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他的不尊重,一种变相的“弑父”情结。我从未真正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他对于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有着怎样深沉的、如同父亲对孩子般的感情。他害怕的不是变革,而是害怕自己毕生的心血被轻易否定,害怕自己被时代抛弃。
长江的教授们也常常在商业案例之外,引导我们思考企业的终极价值、企业家的社会角色和个人的人生目标。这种“取势、明道、优术”的哲学思辨,让我跳出了父子关系的狭隘视角,开始从一个更宏大的人生维度去看待我们的关系。父亲是上一代企业家的缩影,他们用勤劳、坚韧和惊人的商业直觉,抓住了时代给予的机遇,为我们这一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不是去颠覆和否定,而是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去传承和创新。这不仅是企业的传承,更是精神的延续。
如今,我与父亲可以一起在办公室讨论到深夜,也可以在周末的午后一起喝茶闲聊。工厂里的一些新变化,是在我们父子俩的共识下平稳推行的。父亲甚至会主动向我请教一些关于新媒体营销的问题。那道横亘了二十年的冰墙,终于在理解与尊重的暖流中,悄然融化。
回望这段心路历程,读EMBA的经历无疑是那个关键的催化剂。它带给我的,远不止于商业知识和精英人脉。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得以: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最高级的管理,首先是管理好自己;最成功的商业,离不开和谐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与我们最亲近的人。 对于许多像我一样,成长于企业家家庭的“创二代”而言,我们与父辈的矛盾,是两代人价值观、知识结构和时代背景碰撞的必然结果。而打破僵局的关键,或许就在于我们是否愿意主动去学习、去成长,去获得一个更高的认知维度,从而能够俯瞰全局,看清问题的本质。
这场迟到了二十年的和解,让我失去的岁月无法复返,但它让我们的未来,充满了温暖与可能。这或许是我在EMBA学习中,获得的最宝贵的一笔“投资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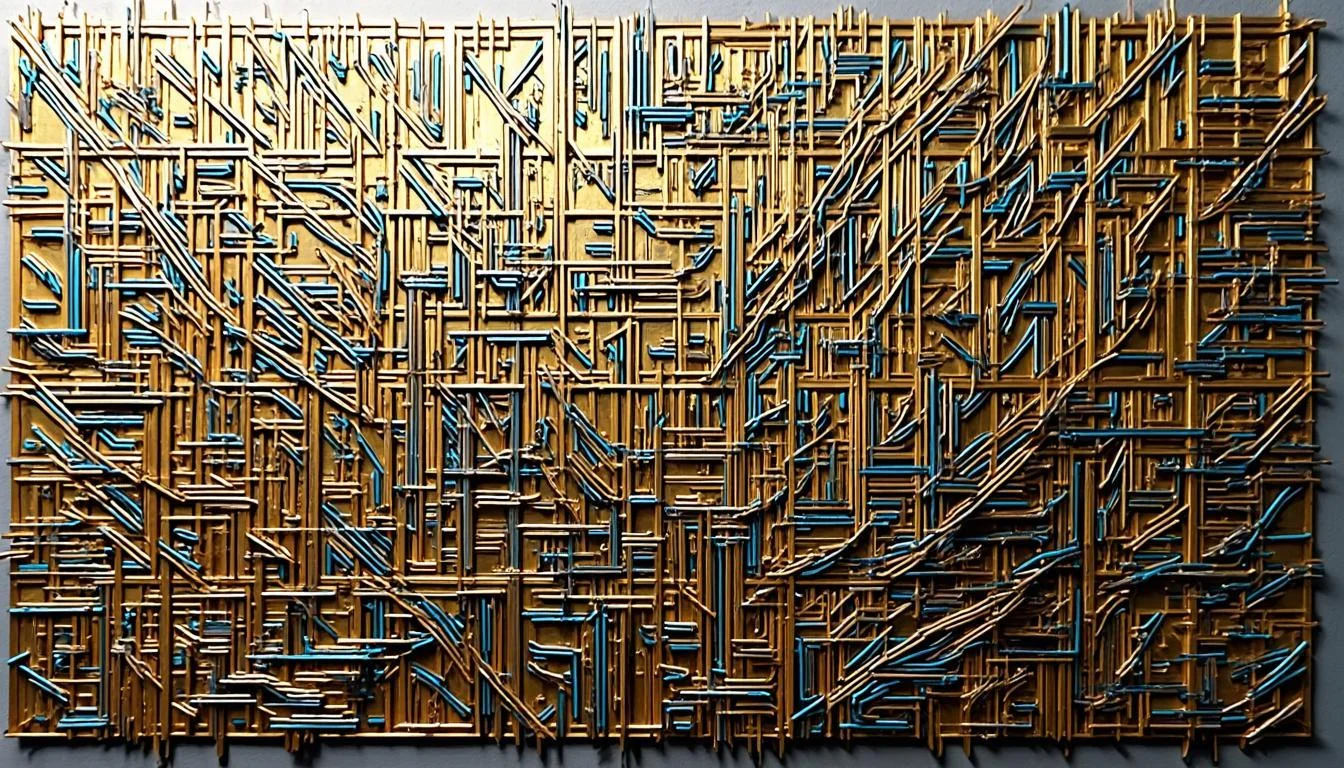
 同窗共度,携手追梦 |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
同窗共度,携手追梦 |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新生万物|听说,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
新生万物|听说,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
申请条件:
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背景(毕业3年以上)、国民教育大专学历(毕业5年以上)
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少于5年核心决策层的管理经验

长江商学院EMBA
关注官微
了解更多课程资讯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