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那封印着“长江商学院”烫金字样的录取通知书静静躺在桌上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激动与自豪。那不仅仅是一纸凭证,更是对过往职业生涯的肯定,和通往更高阶认知殿堂的门票。我憧憬着与各界精英激荡思想,在顶尖教授的引领下重塑商业认知,为自己的事业版图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彼时的我,沉浸在对未来的无限遐想中,却忽略了这趟为期两年的“自我增值”旅程,背后隐藏着一张对家人的巨额“负债单”。两年后,当我手握毕业证书,回望来时路,一个问题反复叩问我的内心:这730个日夜,我究竟欠了家人多少句“对不起”?
在职EMBA,意味着一场对个人时间管理的极限挑战。它像一个精密的榨汁机,将我本就紧凑的日程表里最后一点“自由”也榨取得干干净净。每个月,总有那么一个周末,我需要像候鸟一样飞往另一个城市,沉浸在堆积如山的案例、激烈的小组讨论和高强度的课堂学习中。而这些周末,本应是属于家人的“黄金时间”。
我清楚地记得,儿子不止一次在周五的傍晚,拉着我的衣角,用带着一丝祈求的语气问:“爸爸,这个周末你又要去‘上学’吗?你答应陪我去的科技馆什么时候才能去?” 每当这时,我只能蹲下身,抚摸着他的头,给出一个模糊而遥远的承诺。那句脱口而出的“对不起,爸爸下下个周末一定陪你去”,说出口的瞬间,我自己都感到心虚。因为我知道,下下个周末,或许有同样重要的课程报告或者团队作业在等着我。我欠下的,是孩子童年里本该由我参与的无数个“第一次”——第一次看懂星座图的兴奋,第一次拼好复杂乐高的骄傲,第一次在运动会上跌倒后爬起来的坚强。这些瞬间,我都在“远方”,都在为了一个看似更宏大的目标而“缺席”。
对妻子的亏欠,则更为深沉和复杂。她不仅是我梦想的坚定支持者,更是我缺席后家庭运转的唯一支柱。当我在课堂上与同学探讨着最新的商业模式时,她可能正独自带着发烧的孩子在医院排队;当我在晚宴上与行业大咖举杯交流时,她可能正一个人面对着漏水的马桶和一堆待洗的衣物。我欠她的,是无数个本该共同分担的夜晚,是无数次她疲惫时一个温暖的拥抱,是她需要倾诉时一个耐心的聆听者。我的“在场”,变成了微信里几句匆忙的问候;我的“分担”,变成了“辛苦你了”这样苍白无力的客套话。这种物理上的缺席,日积月累,逐渐在我和家人之间,挖出了一条名为“陪伴”的鸿沟。
如果说时间的缺席是显性的亏欠,那么精力的透支和情绪的负债,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伤害。EMBA的学习强度远超想象,它要求你在处理好全职工作的同时,投入堪比全日制学生的热情和精力。白天,我是公司里运筹帷幄的管理者;夜晚和周末,我变身回为分数和观点争得面红耳赤的学生。这种双重身份的切换,像一根持续紧绷的弦,耗尽了我所有的心力。
于是,我把最疲惫、最不耐烦的一面,不自觉地留给了最亲近的家人。当妻子兴致勃勃地和我分享白天遇到的趣事时,我可能正因为一个复杂的财务模型而心烦意乱,敷衍地“嗯”一声,眼神却从未离开过电脑屏幕。当孩子拿着画笔希望我评价他的“大作”时,我可能因为一篇论文毫无头绪而厉声喝止:“没看我正忙吗?自己去玩!” 话音落下的瞬间,我看到了他们眼中闪过的失落和委屈,心中涌起的悔意像针一样扎人。那一刻,我欠下的“对不起”,是为了自己无法控制的坏情绪,为了将学习和工作的压力转嫁给了无辜的他们。

心理学上的“工作-家庭冲突” (Work-Family Conflict) 理论指出,当一方在工作或学习领域投入过多资源(时间、精力)时,必然会削弱其在家庭领域中的角色表现。我的情况正是这一理论的真实写照。我透支了所有的精力去追逐个人成长,却在家庭这个“情感银行”里不断“取款”,鲜有“存款”。每一次不耐烦的叹息,每一次敷衍的回答,都是一笔笔情绪上的负债。这些负债累积起来,足以侵蚀最稳固的家庭关系,而偿还它们,需要的远不止一句简单的道歉。
我的EMBA求学路,表面上是我一个人的奋斗,实际上却是整个家庭,尤其是我的妻子,在背后做出的巨大而无声的牺牲。这份牺牲,具体体现在家庭责任的全面转移上。在我攻读EMBA之前,我们的家庭分工是相对平衡的。但从我开学的那一刻起,这个天平就发生了严重的倾斜。
为了让我能心无旁骛地学习,妻子主动扛起了几乎所有的家庭责任。下面这张简单的表格,或许能最直观地反映出这两年的变化:
| 家庭责任 | 读EMBA前 | 读EMBA中 |
| 孩子上学接送与课外班 | 夫妻分担,协商安排 | 妻子全权负责 |
| 辅导家庭作业 | 共同负责,各有侧重 | 妻子为主,我偶尔远程视频指导 |
| 周末家庭活动 | 定期策划与执行 | 几乎停滞,视我的课程安排而定 |
| 双方父母的探望与照顾 | 共同前往 | 多由妻子代我尽孝 |
| 个人休闲与社交 | 各自拥有并相互支持 | 我的社交围绕同学,妻子的社交大幅减少 |
这张表格里的每一个“妻子全权负责”,背后都是她个人时间的牺牲和精力的付出。她可能因此放弃了自己心仪的瑜伽课,推掉了与闺蜜的下午茶,甚至搁置了自己职业发展的机会。她用自己的“退”,换来了我的“进”。这份沉甸甸的牺牲,是我最难用一句“对不起”来偿还的。因为我知道,这句道歉背后,是她两年青春里无数个被琐事填满的日夜,是她默默咽下的所有委屈和疲惫。
除了时间和精力上的亏欠,EMBA还带来了一种更深层次的、不易察觉的家庭挑战——认知的错位与成长不同步。在长江商学院的课堂上,我与各行各业的精英们探讨着宏观经济、企业战略、全球化趋势和资本运作。我的思维模式、话语体系,甚至是对世界的看法,都在以一种极快的速度迭代和升级。
当我兴冲冲地回到家,试图分享课堂上学到的“波特五力模型”或者“蓝海战略”时,迎来的往往是家人善意但茫然的眼神。我谈论的“护城河”与“第二曲线”,在他们听来,可能就像是另一个星球的语言。渐渐地,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在减少。我关注的是产业的未来,而妻子更关心的是孩子下学期的学费和家里水电费的账单。这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我们所处的“世界”在悄然间发生了分离。这种认知的“时差”,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也让家人感到了一丝被疏远的隔阂。
这种成长,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我可能在不经意间,用一种“更高”的视角去审视家庭生活,对一些琐事表现出不耐烦。我可能会觉得妻子的担忧“格局太小”,或者无法理解她为什么会对邻里间的八卦感兴趣。这种无意识中流露出的“优越感”,是对家庭情感最微妙的伤害。我欠下的“对不起”,是为了我只顾着自己向前奔跑,却没有学会放慢脚步,耐心等待、引导和分享,没有努力去搭建一座桥梁,来弥合我们之间因成长速度不同而产生的认知鸿沟。
回首在职读EMBA的那两年,要问我到底欠了家人多少句“对不起”?答案是:数不清。每一句“对不起”的背后,都对应着一个被牺牲的家庭时刻,一次被忽略的情感需求,一份被转移的家庭责任。
然而,这篇文章的目的并非沉溺于愧疚与自责,而是为了进行一次深刻的复盘与致敬。它让我清醒地认识到:
如今,EMBA的学业已经结束,但家庭的“课程”永不毕业。对我而言,未来的研究方向和行动指南,就是如何更好地将“对不起”转化为“我爱你”:
读EMBA那两年,我或许亏欠了家人无数句“对不起”。但从毕业那天起,我将用余生的每一天,去告诉他们——“谢谢你”和“我爱你”。因为是他们的牺牲与成全,才让我成为了今天这个更好的自己。而这份因爱而生的亏欠,终将化为更坚固、更温暖的家庭羁绊,指引我们共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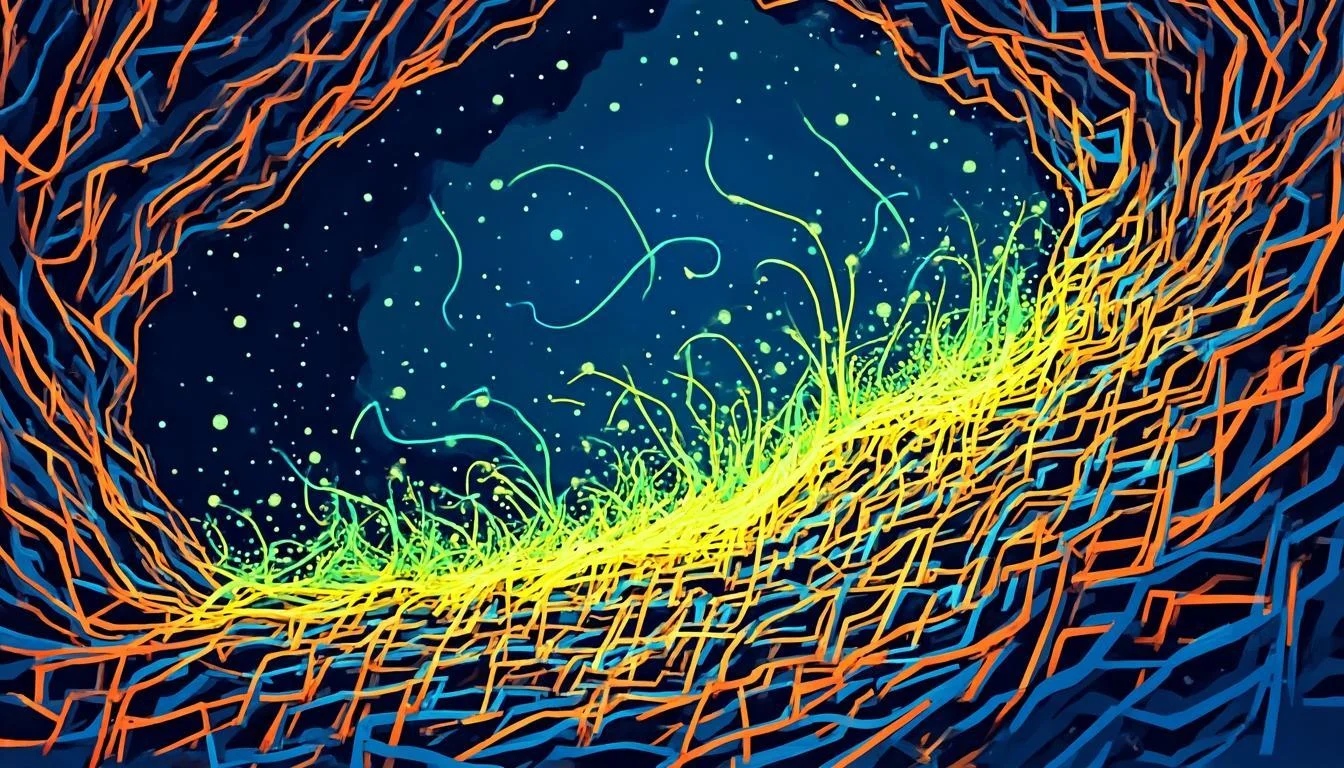
 同窗共度,携手追梦 |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
同窗共度,携手追梦 |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新生万物|听说,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
新生万物|听说,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
申请条件:
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背景(毕业3年以上)、国民教育大专学历(毕业5年以上)
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少于5年核心决策层的管理经验

长江商学院EMBA
关注官微
了解更多课程资讯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