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的,请看下面为您撰写的文章。
在踏入长江商学院的大门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人生赢家”。三十多岁,一家小有成就的科技公司CEO,手握几项核心专利,口袋里揣着几轮融资,张口闭口都是“用户增长”、“算法模型”、“迭代思维”。我以为自己掌握了通往商业圣杯的密码——技术和逻辑。我来读EMBA,初衷很“朴素”:学点管理工具,结识些人脉,最好能给公司再拉一两笔投资。然而,我万万没想到,等待我的不是一次知识的“升维”,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降维打击”。这并非是说我受到了排挤或轻视,恰恰相反,这是一种认知上的猛烈撞击,它打碎了我固有的思维框架,然后逼着我在一片废墟之上,重新构建对商业、对世界、乃至对自己的理解。
作为一个典型的技术人,我的世界观是建立在代码和数据之上的。万物皆可量化,凡事必有逻辑。在我看来,商业决策就像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只要变量给得足够多,数据足够精确,就一定能算出一个“最优解”。我习惯于用A/B测试来验证每一个产品细节,用数据看板来监控每一次市场波动,我坚信,只要我的模型足够完善,就能预测未来,掌控全局。
然而,在长江商学院的第一堂案例课上,我的这种信念就被击得粉碎。教授抛出一个复杂的商业困境,涉及市场、政策、竞争对手和内部人事等诸多因素。我立刻打开电脑,试图建立一个决策模型,量化所有风险和收益。可当我还在吭哧吭哧地计算“最优路径”时,同学们——那些来自传统制造业、金融投资、房地产等领域的大佬们——已经开始了热火朝天的讨论。他们不谈公式,不谈模型,他们谈的是“人性”,是“时机”,是“取舍”,是“灰度”。一位做实业的同学说:“商业世界里哪有那么多最优解?更多的是在信息不完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满意解’。”
那一刻,我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我意识到,我引以为傲的逻辑和算法,在处理复杂的人性和模糊的现实面前,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商业的本质,不是在确定的规则下寻找最优答案,而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混沌中,凭借直觉、经验和对人性的洞察,做出最不坏的决定。这种从“工程师思维”到“企业家思维”的转变,是我在这里受到的第一次“降维打击”,它让我明白,真实的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二进制,而是充满了需要妥协和平衡的灰色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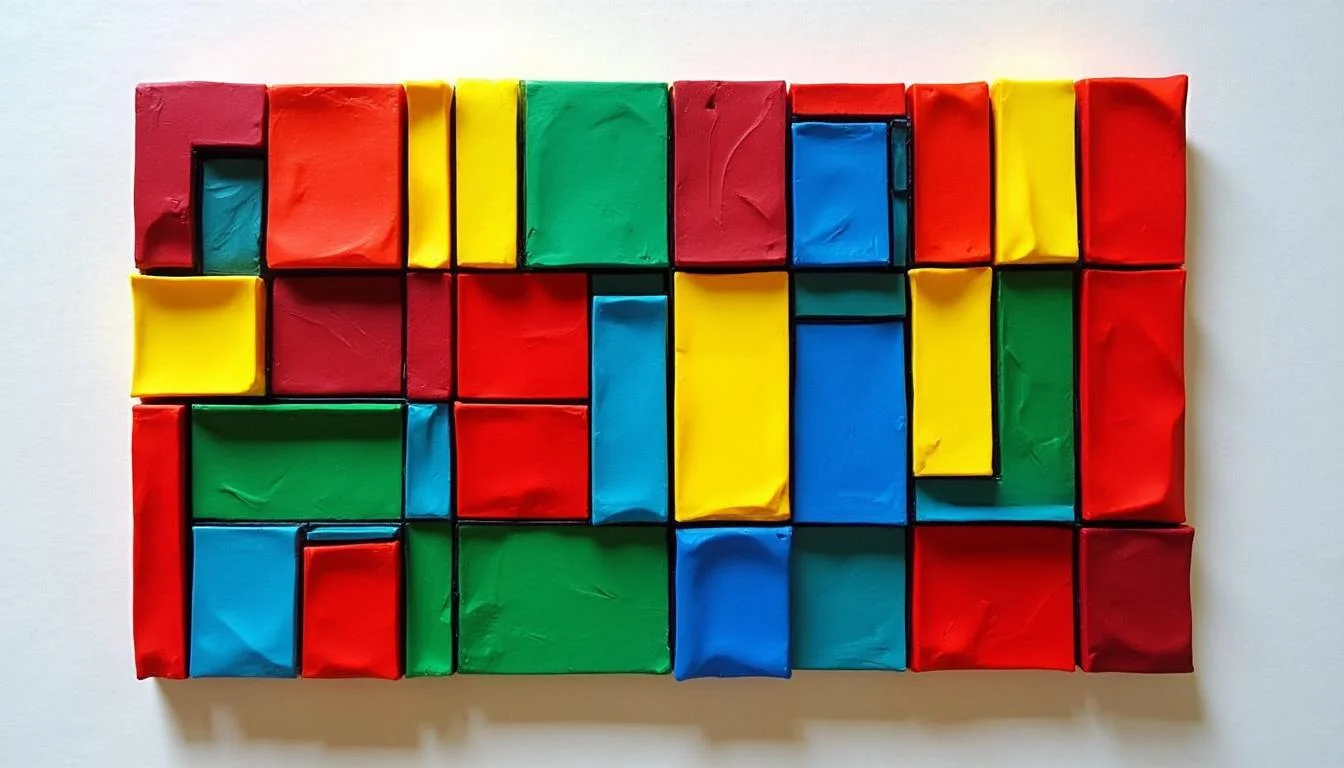
来之前,我对EMBA的人脉充满期待。我把它想象成一个巨大的“资源池”,我需要技术人才,这里有;我需要渠道伙伴,这里有;我需要投资,这里更有。我的社交逻辑非常直接:高效链接,等价交换。我甚至准备好了一份“社交KPI”,计划在两年内认识多少人,达成多少项合作。
但很快,我又“被打脸”了。开学不久的一次小组活动,我们被要求在没有任何商业目的的前提下,分享各自人生中最失败的一次经历。我扭扭捏捏地讲了一个技术攻关失败的故事,而我身边那位平时不苟言笑的地产集团董事长,却坦诚地分享了他早年创业失败、濒临破产的窘境,讲到动情处甚至眼泛泪光。那个晚上,我们没有交换一张名片,却感觉彼此的距离被前所未有地拉近了。我突然明白,真正高质量的人脉,不是建立在功利性的资源互换上,而是建立在信任、共情和价值认同的基础上。
在长江商学院的圈子里,“我是谁”远比“我有什么”更重要。大家更关心你的格局、你的视野、你的为人。你的人脉价值,不在于你能从别人那里索取什么,而在于你能为这个集体贡献什么独特的价值。这种价值,可能是你的行业洞察,可能是你的创新精神,也可能仅仅是你的人格魅力。这种从“索取式社交”到“贡献式社交”的认知升级,是第二次“降维打击”。它让我从一个精于计算的“资源猎手”,开始学着做一个懂得分享和付出的“生态共建者”。
| 维度 | 我过去的技术圈思维 | 长江EMBA的商业生态思维 |
| 核心逻辑 | 功能实现,效率至上 | 价值共创,生态平衡 |
| 关系基础 | 项目合作,资源互换 | 信任背书,情感链接 |
| 价值衡量 | 你能为我做什么?(What's in it for me?) | 我能为大家贡献什么?(How can I contribute?) |
| 社交模式 | 点对点,强目的性 | 网状,长期主义 |
作为一家创业公司的CEO,我自认为很懂“钱”。我能把商业计划书写得天花乱坠,能和VC(风险投资人)唇枪舌战几个小时,对各种估值模型、股权结构设计也算驾轻就熟。我眼中的“钱”,就是支持公司活下去、发展壮大的“燃料”。
然而,在金融教授的课堂上,我才发现,自己那点儿引以为傲的融资知识,在真正的资本大鳄面前,简直就是幼儿园级别的算术。当同学们开始讨论“杠杆收购(LBO)”、“并购基金(M&A Fund)”、“二级市场套利”时,那些陌生的术语和复杂的交易结构,让我感觉自己像个闯入华尔街的“土包子”。我过去理解的“钱”是静态的、是工具性的;而他们口中的“资本”,是动态的、是战略性的,它能像水一样渗透到产业的每一个毛孔,也能像武器一样重塑整个行业的格局。
有一次,一位做投资的同学分享他如何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资本运作,将一家濒临倒闭的传统企业盘活,并最终推向资本市场。他讲的不是产品,不是技术,而是现金流的重组、资产的剥离和注入、以及对市场情绪的精准把握。我听得目瞪口呆,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一家公司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它的产品和市场上,更体现在它的资本结构和运作能力上。这次“降维打击”让我明白,从“找钱”的创业者,到“玩钱”的企业家,中间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而这道鸿沟,需要用全新的金融思维和资本格局去填平。
在科技行业,我们最常说的一个词是“专注”。我们信奉“单点极致”,要把一个产品、一个功能做到最好,从而穿透市场。我的战略视野,很长一段时间都局限在我的赛道、我的用户、我的竞争对手这“一亩三分地”里。我关心的是下个季度的用户增长率,是对手又发布了什么新功能。
但在长江商学院,教授和同学们讨论的,却是完全不同维度的话题。他们会花一整天的时间去探讨“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会分析“地缘政治风险如何重构全球供应链”,会从历史的周期中去寻找企业发展的规律。我记得一位教授在课堂上问:“五年后,决定你公司生死的,是你今天开发的功能,还是你今天没有看到的某个宏观趋势?”
这个问题让我醍醐灌顶。我一直低头拉车,却忘了抬头看路。我所处的行业,不过是整个社会经济大图景中的一个像素点,它的兴衰荣辱,无时无刻不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在这里,我学到的最重要的战略课是:
这种从“战术勤奋”到“战略懒惰”的警醒,是又一次深刻的“降维打击”。它把我的视线从脚下的土地,强行拉向了遥远的天际线,让我开始思考那些更大、更根本、也更决定命运的问题。
两年时间,我带着一身的技术人傲气走进长江商学院,最终却像一个被彻底“格式化”的硬盘,带着全新的操作系统走了出来。“降维打击”这个词,听起来似乎有些残酷,但对我而言,它却是一次无比珍贵的成长洗礼。它不是否定我过去的成功,而是打破我成功的路径依赖,为我打开了无数个新的可能性维度。
我在这里学到的,远不止是管理知识和商业工具。更重要的是,我完成了一次从“专才”到“通才”,从“管理者”到“领导者”的认知蜕变。我学会了用更复杂、更多元的视角去看待商业,用更谦卑、更开放的心态去面对世界,用更温暖、更具同理心的方式去理解他人。
如果你问我,对那些和我一样有技术背景、正考虑是否要踏入商学院的CEO们有什么建议?我的建议是:请务必做好被“降维打击”的准备。请放下你的代码,忘掉你的模型,清空你的“最优解”执念。带着一颗空杯心态,去拥抱那些模糊、混沌和不确定性,因为在那片你曾经最不屑的“灰色地带”里,恰恰隐藏着一个企业家成长所需的最宝贵的养分。这不仅仅是一次学习,更是一次关乎格局和视野的自我重塑。

 同窗共度,携手追梦 |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
同窗共度,携手追梦 |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新生万物|听说,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
新生万物|听说,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
申请条件:
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背景(毕业3年以上)、国民教育大专学历(毕业5年以上)
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少于5年核心决策层的管理经验

长江商学院EMBA
关注官微
了解更多课程资讯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