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个“颠覆”一词几乎被用滥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被各种新概念、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轮番轰炸。从共享单车到人工智能,从新零售到元宇宙,似乎每一个创业者都手握着颠覆世界的剧本。而对于那些已经在商海中乘风破浪多年的企业家和高管们来说,焦虑感与日俱增: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颠覆的“柯达”或“诺基亚”?于是,各大商学院的“颠覆式创新”课程应运而生,其中,长江商学院EMBA的相关课程更是备受瞩目。但一个核心问题始终萦绕在人们心头:花上不菲的学费和宝贵的时间,去上一门名为“颠覆式创新”的课,真的能颠覆我们早已固化的商业思维吗?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课程价值的疑问,更是一个关乎个人认知升级和企业未来生存的深刻命题。我们试图从理论框架、课堂体验、实践落地等多个维度,层层剖析这门课程的内核,探讨它究竟是商业精英们的一剂“安慰剂”,还是一场真正能够重塑思维的“认知风暴”。
要评判一门课程能否“颠覆思维”,首先要看它的理论根基是否坚实。如果“颠覆式创新”仅仅是一个时髦的口号,那么任何基于此的教学都无异于空中楼阁。幸运的是,这个概念背后有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等管理学大师构建的严谨理论体系。这套理论的精髓,远比我们通常理解的“用新技术打败老技术”要深刻得多。
课程的核心,首先是帮助学员精确地“重新定义”颠覆。真正的颠覆式创新,往往不是以性能更优、价格更贵的产品去抢占现有市场的高端客户,那被称为“延续性创新”。相反,它通常以更简单、更便宜、更便捷的“足够好”的产品或服务,从市场的低端或边缘地带(即“新市场立足点”或“低端市场立足点”)切入。这些市场被行业巨头们因利润微薄或规模太小而忽略。新进入者在此站稳脚跟后,不断迭代产品,沿着价值网络向上移动,最终蚕食主流市场,让曾经的霸主措手不及。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这一过程:优秀的企业之所以失败,恰恰是因为他们太“优秀”了——他们精于倾听主流客户的声音、专注高利润市场、依赖成熟的流程和价值观,而这些优势在面对颠覆性威胁时,反而变成了致命的枷锁。
在长江商学院的课堂上,教授们会引导学员深入解构这一理论。他们不仅仅是复述定义,而是通过大量的经典案例分析,比如Netflix如何颠覆Blockbuster,个人电脑如何颠覆小型机,让学员们亲手“解剖”这些商业史上的巨变。更重要的是,课程会引入一套分析工具,如“RPV框架”(资源、流程、价值观),帮助学员诊断一个企业是否具备应对或发起颠覆的能力。这种从“是什么”到“为什么”再到“怎么办”的层层递进,将一个看似玄妙的概念,转化为一套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应用的思维模型。这本身,就是对许多人“颠覆=技术突破”的朴素认知的第一次颠覆。
如果说坚实的理论是骨架,那么独特的课堂体验则是血肉,它让知识真正“活”起来。EMBA课程的最大价值之一,从来不只在于教授单向的知识传授,更在于学员之间高水平的互动与激荡。而“颠覆式创新”这一主题,恰好为这种思想碰撞提供了最完美的舞台。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一位来自传统制造业的董事长,正分享他如何通过精益管理将成本控制到极致,并以此为傲。而他邻座的,可能是一位90后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他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免费模式快速获取海量用户,再通过增值服务实现盈利。在教授的引导下,他们会探讨一个尖锐的问题:当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出现,它提供的价值主张并非“更好的质量”,而是“极致的便利”或“零成本的准入门槛”时,那位董事长的“成本优势”护城河还稳固吗?这种跨行业的视角交锋,远比任何书本上的案例都来得直接和震撼。它迫使每个人跳出自己熟悉的“舒适区”,用他人的“望远镜”来审视自己的世界,从而发现那些因身处其中而无法察觉的盲点和偏见。
长江商学院的EMBA学员本身就是一群“身经百战”的商业领袖,他们带来的不仅是问题,更是鲜活的、正在进行时的“商业案例”。在课堂讨论中,教授的角色更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催化剂”和“导演”。他会巧妙地将理论模型与学员的实际困境相结合,比如,当一位零售业巨头的高管在为线上冲击而烦恼时,教授可能会引导大家思考:“你的公司之所以难以转型,是缺乏资源(钱、人、技术)?还是固有的流程(KPI考核、供应链管理)在阻碍?亦或是公司的价值观(追求高毛利、服务高端客户)让你无法拥抱低端市场?”这种直击灵魂的追问,往往能引发学员深刻的自我反思。思维的颠覆,正是在这一次次激烈而真诚的辩论、反思和共创中悄然发生的。
在一门旨在“颠覆思维”的课程中,教授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绝不能是高高在上的“真理布道者”,而应是谦逊的“思想引路人”。他们的任务不是给出标准答案,而是提出好的问题,挑战学员根深蒂固的假设,并搭建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大家去探索和试错。
优秀的教授会像一位苏格拉底式的导师,通过不断追问,引导学员自己找到答案。例如,他不会直接评判某个学员公司的战略“是对是错”,而是会问:“如果你的核心假设(比如‘客户永远需要最高性能的产品’)是错的,那会怎么样?”“有没有一个被你忽略的客户群体,他们的需求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就能满足?”“如果你要成立一个内部团队去颠覆自己的主营业务,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资源、流程和自由度?”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切开思维的壁垒,暴露出那些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背后的脆弱性。
此外,长江商学院的教授团队往往具备“全球视野”与“中国洞察”的双重优势。他们既能引介克里斯坦森等国际大师的原汁原味的理论,又能结合中国本土瞬息万变的商业实践,提出富有洞见的分析。他们可能用拼多多、抖音的崛起,来生动诠释“低端市场立足点”和“新市场立足点”的威力;也可能用华为的自我变革,来探讨大企业如何通过组织创新来避免“创新者的窘境”。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无缝对接,让课程内容既有学术的深度,又有极强的现实关照。学员们学到的不只是一个“舶来”的理论,而是一套能解释自己身边正在发生的商业奇迹、并能指导自己未来行动的思维工具。
“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这是知识学习中最大的痛点。一门课程无论在理论和课堂上多么精彩,如果不能转化为学员的实际行动,那么所谓的“思维颠覆”也只是一场短暂的头脑体操。因此,衡量“颠覆式创新”课程成败的关键,在于它能否有效地帮助学员跨越从“知道”到“做到”的鸿沟。
课程通常不会在结课时就画上句号。它更像是一个起点,开启了学员对自己企业进行“颠覆式诊断”的旅程。许多课程会设置后续的行动学习项目,要求学员将课堂上学到的框架和工具,应用到自己公司的实际挑战中去。这才是最艰难,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在课堂上分析别人公司的失败案例总是轻松的,但要亲手解剖自己引以为傲的成功业务,去寻找其中可能存在的“颠覆基因”,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清醒的头脑。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种思维转变,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表格来对比传统思维与颠覆式思维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的差异:
| 商业维度 | 传统延续性思维 | 颠覆式创新思维 |
|---|---|---|
| 目标客户 | 关注我们最大、最重要、利润最高的客户。 | 寻找那些被现有产品“过度服务”的低端客户,或根本不是我们客户的“非消费者”。 |
| 产品开发 | 在现有产品基础上增加更多功能,追求更高性能。 | 开发更简单、更便宜、更便捷的“足够好”的产品。 |
| 市场评估 | 如果市场看起来太小,或者不确定,就放弃。 | 将市场小视为一个优势,因为它不会引起行业巨头的注意。这是颠覆的“保护伞”。 |
| 资源分配 | 将最好的资源投入到最确定的、回报率最高的项目中。 | 为颠覆性项目建立一个独立的、拥有自主权的组织,保护它不受主流业务流程和价值观的扼杀。 |
| 衡量成功 | 用现有的财务指标(如毛利率、投资回报率)来衡量新业务。 | 初期更关注学习和验证,而非盈利。衡量指标是“我们学到了什么”而不是“我们赚了多少钱”。 |
当一位企业家开始用右侧的逻辑去审视机会时,他的世界观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看到的不再仅仅是现有市场的红海竞争,而是被忽略的蓝海空间;他思考的不再仅仅是如何“防御”,而是如何主动“出击”,甚至是如何“自我颠覆”。这门课程提供的,正是这样一套全新的“作战地图”和“导航系统”。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长江EMBA的“颠覆式创新”课程,真的能颠覆你的思维吗?
答案是肯定的,但这并非一种魔术般的“顿悟”,而更像是一场艰苦但收获巨大的思维“拆解与重建”工程。它不能保证你第二天就能想出一个颠覆性的商业创意,但它能为你提供以下几样至关重要的东西:
最终,思维的颠覆与否,主动权仍然掌握在学员自己手中。如果仅仅是抱着“听听看”的心态,那么再好的课程也只是过眼云烟。但如果学员带着真实的企业困惑而来,以开放的心态拥抱挑战,并有勇气将所学付诸实践,那么这门课程所点燃的火花,完全有可能燎原,不仅颠覆其个人思维,更能深刻地影响其企业的未来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投资的不是一门课程,而是投资了一种在不确定时代中持续进化、保持领先的底层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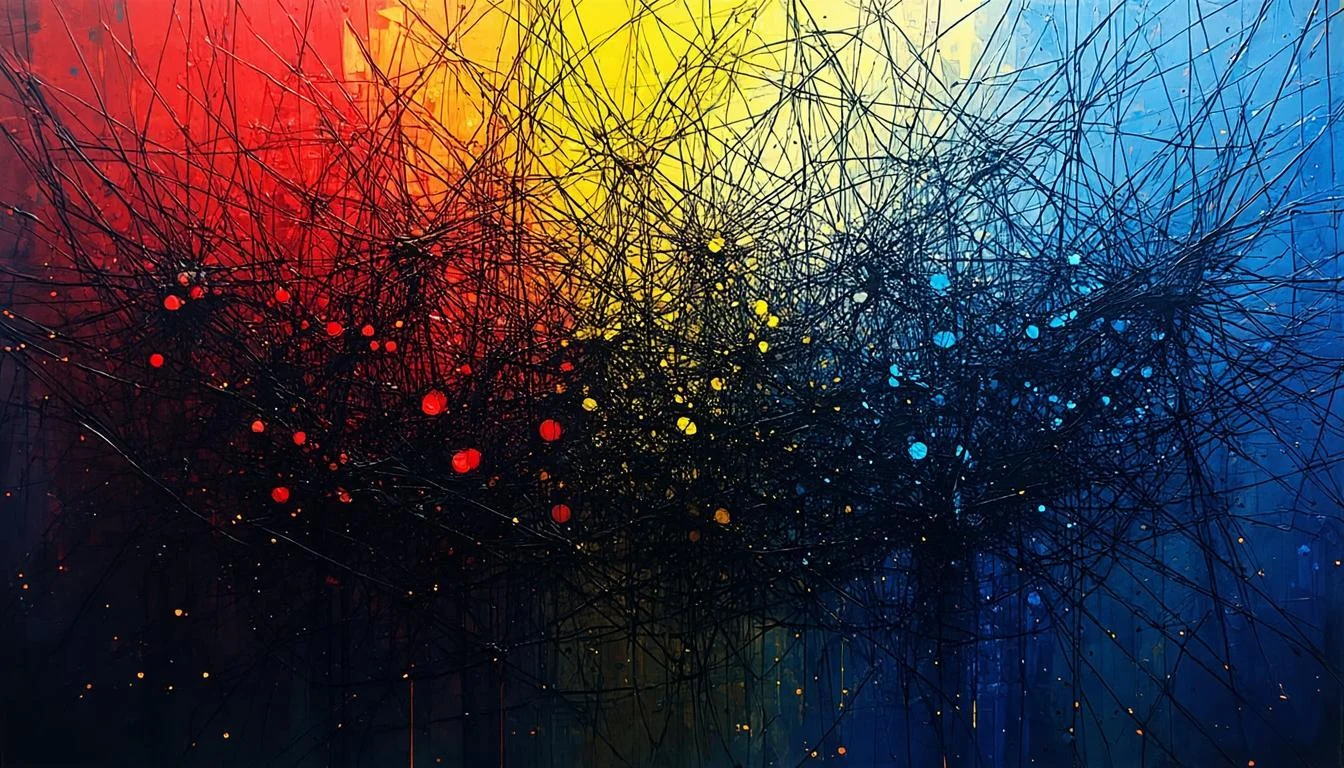
 同窗共度,携手追梦 |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
同窗共度,携手追梦 |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新生万物|听说,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
新生万物|听说,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
申请条件:
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背景(毕业3年以上)、国民教育大专学历(毕业5年以上)
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少于5年核心决策层的管理经验

长江商学院EMBA
关注官微
了解更多课程资讯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