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让我重新回到长江商学院那间坐满了行业翘楚的EMBA教室,我一定会对自己说:“别那么‘乖’!”。多年后的今天,当我抚摸着那本精致的毕业证书,回想起那些在聚光灯下的教授、那些激荡思想的案例,心中涌起的却并非满满的成就感,而是一种深刻而清晰的遗憾。我最后悔的,就是在长江EMBA的课堂上太“乖”了。这种“乖”,不是指遵守纪律,而是指一种思维上的循规蹈矩,一种互动上的被动和胆怯,它让我像一个精致的海绵,吸饱了知识的表层水分,却错过了潜入深海探寻宝藏的机会。
在长江EMBA的课堂上,我曾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学生”。教授讲的每一个理论模型,我都会认真记下;小组讨论的每一个案例,我都会用最经典的框架去分析。我发言,但说的都是确保“政治正确”的观点;我提问,但问的都是能被轻易解答的“安全”问题。我害怕自己的提问显得“小白”,害怕在这些CEO、创始人、投资人同学面前暴露自己的无知。这种对“无知”的恐惧,像一道无形的枷锁,锁住了我思想的野性。
回过头看,这恰恰是最大的认知误区。EMBA教育的核心价值,并不仅仅是知识的单向灌输,更在于通过碰撞、质疑和挑战,重塑每个人的思维底层代码。哈佛商学院教授艾米·埃德蒙森(Amy Edmondson)提出的“心理安全感”(Psychological Safety)理论指出,一个高效的团队或学习环境,必须让成员感到可以安全地展示脆弱、承认不足。而我当时的“乖”,正是缺乏心理安全感的典型表现。我将课堂视为了一个需要展现完美的舞台,而不是一个可以犯错、可以“冒犯”权威、可以自由探索的实验室。我忘了,那个看似“愚蠢”的问题,往往能刺破习以为常的思维茧房,引出一场真正有价值的深度讨论。
真正的学习,始于“冒犯”。不是无礼的挑衅,而是对既定答案的勇敢质疑。当教授抛出一个经典的波特五力模型时,我内心其实在嘀咕:“这个模型在今天这个快速迭代的互联网时代,还完全适用吗?边界在哪里?”但我没敢问。我怕教授觉得我挑战他,怕同学觉得我哗众取宠。于是,我“乖乖”地接受了,错失了一次将经典理论与前沿实践进行激烈对撞的绝佳机会。这种遗憾,远比考试得高分而带来的满足感,要来得持久和沉重。
来到长江商学院的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带着拓展人脉的目的。我也不例外。刚开学时,我像个雷达,扫描着班级里每一位同学的背景,试图找出谁是“潜在的合作伙伴”,谁在我的“产业链上下游”。我积极地与那些看起来“有用”的同学交换名片,参加他们组织的饭局,聊着关于投资、市场和资源的话题。这种社交方式,高效、直接,但现在看来,却充满了功利主义的短视。
我“乖乖”地遵循着一种世俗的社交法则,却忽略了EMBA同学圈最独特的价值——多元性带来的“弱联系”力量。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弱联系优势”(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理论早已揭示,那些与我们不同领域、不同圈层的人,反而最有可能为我们带来颠覆性的信息和机会。班里那位做艺术品收藏的同学,那位投身公益组织的同学,那位研究古代哲学的同学,在当时的我看来,似乎与我的事业“无关”。我与他们礼貌地打招呼,却很少进行深入的交流。我没有去探寻,艺术品的审美逻辑如何能启发我的产品设计?公益组织的运营模式如何能重塑我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古代哲学中蕴含的智慧又如何能帮助我应对当下的管理困境?

我像一个目标明确的猎人,只盯着那些体型庞大的“猎物”,却错过了整片森林里更丰富的生态和更美丽的风景。真正的顶级人脉,不是你拥有多少张“有用”的名片,而是你能够与多少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建立连接。那些被我忽略的“弱联系”,或许正蕴藏着让我突破瓶颈的“黑天鹅”或“神启”。这种因“乖巧”地执行功利社交而造成的损失,是无法用任何商业合作来弥补的。
在长江的课堂上,教授们会分享大量经典的商业案例,从哈佛到沃顿,从通用电气到苹果。我像所有“乖”学生一样,认真预习,积极讨论,试图从这些已经尘埃落定的故事中,总结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成功密码”。我专注于书本和PPT,将教授视为唯一的知识权威,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身边最宝贵的、流动的知识宝库——我的同学们。
坐在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部正在书写的、鲜活的“商业案例”。他们踩过的坑,远比教科书上的失败总结来得具体;他们抓住的机遇,也比商业杂志的报道来得更加真实和复杂。长江商学院之所以能汇聚群英,其核心价值就在于搭建了一个让这些“活案例”相互碰撞、相互启发的场域。而我,却常常“乖巧”地把课堂时间和课后时间分得一清二楚。课堂上,我们是师生;课后,我们是朋友。我没能真正地、持续地、深入地把他们当作研究对象,去挖掘他们决策背后的心路历程,去探究他们企业文化形成的深层原因。
试想一下,如果我能这样做,学习效果将是天壤之别。下面这个表格,或许能清晰地展现我所错失的:
| 学习维度 | 传统的“乖学生”模式 | 理想的“活案例”模式 |
|---|---|---|
| 知识来源 | 教授、教科书、经典案例 | 教授 + 全体同学的实战经验 |
| 学习场景 | 课堂讨论、小组作业 | 课堂 + 课后私聊、企业互访、深夜酒局 |
| 案例特点 | 静态的、已成定局的、经过美化的 | 动态的、正在发生的、充满细节和挣扎的 |
| 学习目标 | 理解理论、掌握模型 | 理解理论 + 洞察人性、反思自我、解决真实问题 |
我本可以组织“私董会”,让那位深陷供应链危机的同学分享他的焦虑与对策;我本可以在酒后,追问那位成功转型的同学,在最艰难的时刻是如何说服董事会的。这些知识,是任何商学院教材都无法给予的。我“乖巧”地完成了学业,却像一个手捧金饭碗的乞丐,没有真正享用到里面的佳肴。
中国文化崇尚“和为贵”,这在商界领袖的圈子里尤为明显。在课堂上,大家习惯于彼此肯定、相互吹捧,营造一种一团和气的氛围。我也“乖乖”地融入了这种氛围。当一位同学分享他的成功经验时,即使我觉察到其中有幸存者偏差的成分,或是其模式难以复制,我通常也会选择点头微笑,附和几句“了不起”、“有启发”,而不是提出尖锐的、可能让对方尴尬的质疑。
这种“乖”,实质上是对“建设性冲突”(Constructive Conflict)的回避。管理学大师帕特里克·兰西奥尼(Patrick Lencioni)在其著作《团队的五大障碍》中,将“惧怕冲突”列为团队协作的第二大障碍。一个没有冲突的团队,往往是一个没有深度思考和创新的团队。同样,一个没有思想交锋的EMBA课堂,其价值也会大打折扣。真正的尊重,不是无原则的附和,而是在充分思考后,提出真诚的、哪怕是尖锐的反馈。
我后悔没有更勇敢地去扮演那个“魔鬼代言人”的角色。当大家都在为一种新商业模式欢呼时,我本可以站出来,冷静地分析其潜在的风险和伦理问题。当教授的观点与我的实践经验相悖时,我本可以更有条理地陈述我的案例,与他进行一场平等的对话。这样的“冲突”,或许会带来短暂的紧张,但最终会激发更深层次的思考,让真理越辩越明。而我,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为了做一个“情商高”的“乖”同学,放弃了这种宝贵的成长机会。
回顾在长江商学院的求学之旅,我收获了知识、友谊和一张闪亮的文凭。但我内心最深处的遗憾,始终是那个过于“乖巧”的自己。这种“乖”让我错过了思想的极限探险,错过了人脉的深度链接,错过了将知识内化为智慧的蜕变过程。它让我安全地毕了业,却也让我平庸地毕了业。
这篇文章,既是我的自我反思,也是写给所有正在或即将在顶尖商学院求学的朋友们的忠告。如果你有幸进入这样的知识殿堂,请一定记住:
说到底,EMBA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更博学的“好学生”,而是让你成为一个更清醒、更勇敢、更具洞察力的决策者。而这一切,都始于你敢于对那个“乖巧”的自己说“不”。别让多年后的你,也发出和我今天一样的感慨。请在课堂上,做一个勇敢的“坏”学生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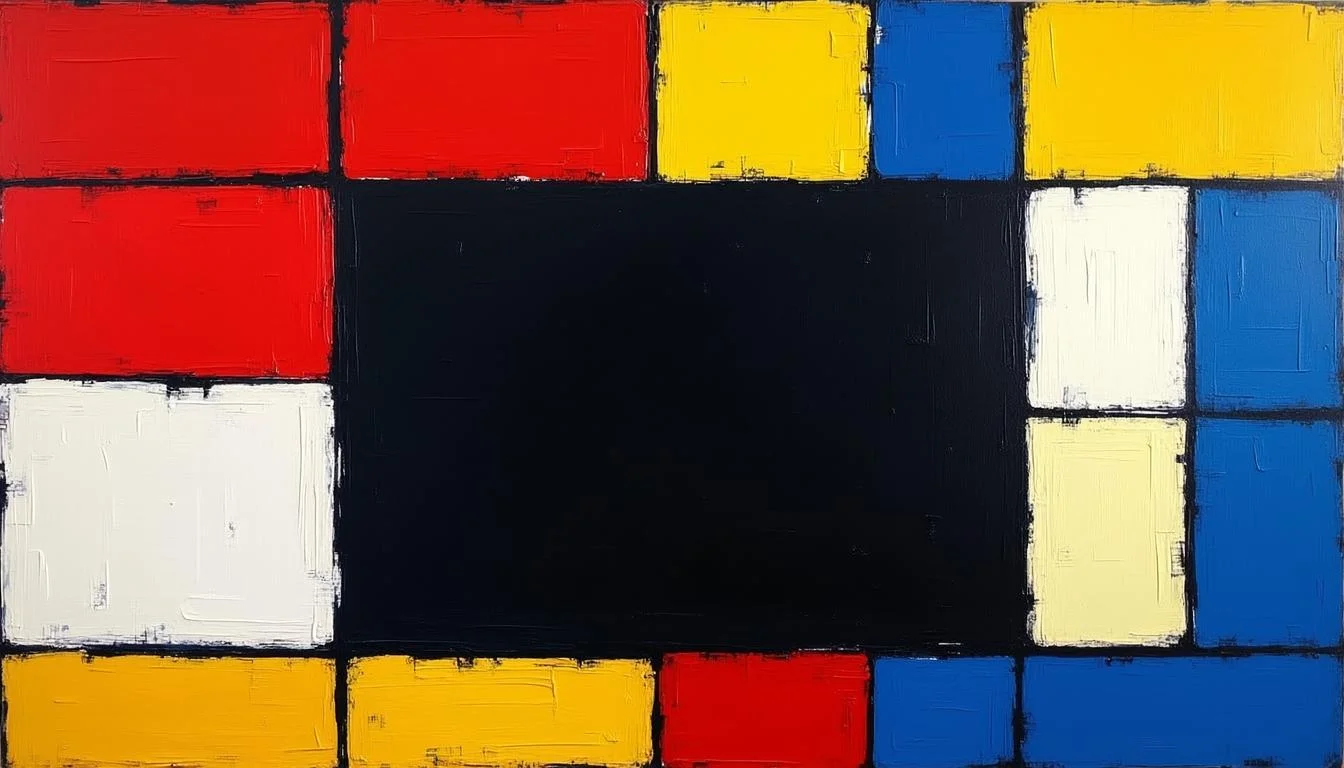
 同窗共度,携手追梦 |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
同窗共度,携手追梦 | 长江商学院EMBA2024秋季1班首次游学之旅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秋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长江商学院EMBA课程|2025春季班入学申请最全攻略
 新生万物|听说,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
新生万物|听说,他们也来读长江EMBA了!
申请条件:
具有国民教育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背景(毕业3年以上)、国民教育大专学历(毕业5年以上)
具有8年或以上工作经验及不少于5年核心决策层的管理经验

长江商学院EMBA
关注官微
了解更多课程资讯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
长江商学院版权所有
京ICP备20005229号 京公网安备11010102000785号